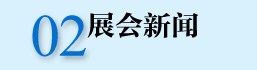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是一份英文汉学杂志,1923年1月由英国籍博物学家苏柯仁联合著名汉学家福开森等创办于上海,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为双月刊,1925年改为月刊。1927年1月,杂志英文名由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改为The China Journal,中文名于1936年1月相应地改为《中国杂志》。至1941年停刊,19年间共出版35卷214期,影响遍及瀛海内外,深受当时汉学界关注。
该杂志系近代西方人在华创办的最重要的汉学杂志之一,创办目的是深化中国科学研究,并且鼓励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研究,重点是支持原创性研究。主要刊登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文章,内容包括动植物及矿产资源调查、生物化工研究、水文气候分析、地理物产调研、政治经济评述、风土人情介绍、时局动态跟踪、艺术宗教以及历史文化研究等等,对于促进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推动近代欧美汉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及学术价值。其所附图像资料尤其丰富美观,弥足珍贵。
与以往乃至同时期的汉学杂志较多关注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化等不同,《中国杂志》刊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文章,从中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20世纪的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使得该刊成为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汉学期刊。
与其他汉学杂志相比,《中国杂志》具有两点特殊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其一,《中国杂志》内容的涵盖面要广泛得多,不仅涉及中国事物的人文方面,亦涉及自然方面;不仅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状况和问题。其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人文与自然的百科全书。其二,值得关注的是,该刊设址上海,对民国年间的上海市况多有记录,蕴含极为丰富的上海地方史资料,比如其对“淞沪抗战”的全程图文报道,内容相当丰富翔实。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早期西文文献十分丰富,在国内首屈一指;然而由于时代较久、流传不广,今天的读者对其知之甚少。加上出于对珍稀文献的保护需要,读者查阅亦有不便。有鉴于此,该馆组织馆内外相关专家,联合馆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将多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西文文献,以“徐家汇藏书楼西文文献丛刊”的形式,予以陆续整理出版。2013年1月推出的在学界反响热烈、35巨册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即丛刊之一种,本次整理出版的《中国杂志》为丛刊之最新一种。
《中国杂志》全书共精装38巨册,其中第一册为导论及总目,导论由著名历史学者、本书学术顾问李天纲教授撰写,详细介绍和解读了杂志的出版情况、编撰特点、主要内容及史料价值等;总目详列所有35卷共214期杂志所刊载文章的中英文篇名、作者名、专题分类以及发表年月、所在卷期和页码等。第2~37册为所有原刊之全文影印,影响效果上佳,殊为清晰美观。第38册为全书索引,共包括专题索引、篇目索引和作者索引等三个不同检索方式的索引,极便读者查阅利用。为方便普通读者了解《中国杂志》的概貌,出版方特将第1册《导论·总目》卷另行单独印行。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今次《中国杂志》的影印出版,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而重要的资料,对于推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国新闻史研究等,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附录:《中国杂志导论》摘要(李天纲)
学术研究与知识启蒙:缘起和宗旨
《中国杂志》的初衷是办一份研究刊物,为西方学者(也包括增多的华人学者)提供发表园地;同时,也兼带普及中国科学和艺术知识的职能,以激发公众的学术兴趣。从《中国杂志》的19年经历来看,这是一份兼具学术探索和社会责任双重功能的杂志。由于中国社会的需求,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兼顾专业与普及、学术与社会的初衷,越来越朝后者的方向倾斜,时事评论的内容不断增加。1938年杂志改组之后,《中国杂志》最终转型为一份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兼具社会、时事和文化内容的综合性杂志。
中国近代知识界除了需要利用科学,发明“新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把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转型为人类通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任务涵盖面广,仅仅一个学科,哪怕是一个庞大学科也远远不够。中国文化要全面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就要众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来推动,中国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文报刊繁荣,思想领袖们在提倡“文明”、“启蒙”和“科学”等进步观念,但真正能够用科学精神来推进科学研究的人并不多。在躬身科学(数学、天文、声光化电)方面,“戊戌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还不及“同光一代”(容闳、马相伯、马建忠、严复)那么刻苦,“辛亥一代”(孙文、章太炎)和“五四一代”(陈独秀、胡适)等也未见得有多大的进步。这当然是指所谓的“风气”、“思潮”中的代表人物而言,事实上1920年代的中国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任鸿隽、胡敦复、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没有产生真正的“启蒙”成效,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普及和宣传。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中国杂志》这样的文化杂志,哪怕是用英文出版,或者仅仅惠及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精英人群。
《中国杂志》:中国的杂志
关于《中国杂志》的身份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它是一份中国杂志。《中国杂志》用英语撰写和出版,它的读者有很多却是中国人。不惟如此,我们说《中国杂志》是一份中国杂志,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即它的编者和作者都有较强的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经历与认同。分析它的创刊号作者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杂志固然是由中外籍贯的英文作者主持的,但这些人和中国(或者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8年之前的《中国杂志》,基本上是一般同仁刊物通行的撰稿人制度,作者都是相对固定的圈内人。既然是以苏柯仁周围的生物、地质学家为主,自然也是英、美籍裔人较多。但是,在约稿和投稿的作者中,华裔、华人作者所占的比例不少,且连续不断,不断有新的作者加入。这些作者,都是各学科的一流人选,通观《中国杂志》的华人、华裔作者名单,大部分是在上海和通商口岸地区的教会大学、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学者,许多是有留学背景,或从海外来到大陆。伍连德、洪深、辜鸿铭、袁同礼、唐绍仪、江文汉、黎照寰、俞大絪、竺可桢等人属之,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具有全局影响力。这类学者用英文写作,不假翻译就进入国际学术圈。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学术界,在新式大学里成长起一批现代学者,他们掌握英语,更容易进入现代学术之门。但是,现代学术并不只是掌握外语,更重要在学术内容上创新和更新,这在科学界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杂志》为了发掘中华学术资源,无论是在传统文化(“汉学”)的领域,还是在经验研究(“科学”)的领域,都鼓励和采纳更有价值的学术。《中国杂志》虽然兼有知识普及的功能,但很少刊登国外现成科研成果的介绍。《中国杂志》立足中国的原创性研究,基本上只刊登有关中国的生物、地理、国学、国艺、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的研究。“在华言华”,显然是《中国杂志》的编辑策略,它使得一批华人学者更容易作为作者,参与到刊物中来。
清末民初华人进入世界科学之林,已有伍连德的防疫学成果被提名诺贝尔奖,但主要是区域性的成就,还拿不出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的普世性(Universality)项目。中国的学术杂志要办出国际水准,先应该“在华言华”,重视当地性(Locality)。在这方面,杂志主编苏柯仁和福开森的合作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苏擅长自然科学,人脉局限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福开森的人脉比较多,政治参与深,“汉学”视野广,对中华文明自有体悟。在福开森的主持下,“美术”(“汉学”)栏目先后刊登了江亢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倩人翻译,隆重推出,代表《中国杂志》的学术倾向。
“科学无国界”:民族国家与现代学术
1927年5月,主编苏柯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撰写了一篇社论《科学无国界》(Science Knows No Country):“科学无国界,以及知识的国际化,这是一个已经被二十世纪全人类普遍接受的事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要是还在声称他那落后和过时的文化还可以躲在人类知识体系,维持着某一个角落,或者有权守着一条独自的研究路线,都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世界主义”(普世理想)与“民族主义”(地方情愫)是共生共进的人类主张,两者互为犄角,彼长此消,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遗产。“科学无国界”的口号与“民族有主权”,就是这样的一对关系。对科学家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民族有主权”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科学无国界”则是学者们必须坚持的原理和信念。举例来说,查明中国地壳内部的地理、地质状况,这是全球科学家的义务,属于无国界行为。当地机构利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开发矿产资源,这涉及到地区、民族和国家利益,属于有边界的行为。
苏柯仁和《中国杂志》提倡“科学无国界”,是一种“普世主义”,它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容易理解。但是,科学家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无国界”的纯科学不可能过滤掉所有的地方性,“科学无国界”的普遍原理,必须处理“研究有地方”的客观现实。《中国杂志》既然是关于中国科学、中国文化的学刊,中华文明的地方性就是首要对象。苏柯仁坚持《中国杂志》在“科学”领域的普世性,福开森代表“美术”(文化)领域的地方性。然而,苏柯仁和福开森的态度并不是冲突和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中华文化的地方性,仍然是世界科学和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就好像“北京猿人”研究是人类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Chineseness不可通约。如果出现以国家的名义干预科学研究,压制普遍性的科学行为,这就需要坚持“科学无国界”的原理;然而,一旦出现滥捕“大熊猫”的生物灾难,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出面维护这种“地方性”,因为失去了这种“地方性”,便也没有“普遍性”。在这方面,《中国杂志》采取的态度显然是开明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他们在“普世性”和“地方性”上的处理方法,也是合乎逻辑的。
文理并体:现代学术的方向
《中国杂志》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中文刊名中的“科学”和“美术”,英文是Science和Arts,另一种翻译也可以是“理科”和“文科”。把文科、理科并在一起,是一份综合性、探索性,兼有普及和欣赏价值的学术杂志。从近代学术背景来看,今天人们把人类知识,大致地分为文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大学里定型的。近代欧洲学术起源时按照“文艺复兴”的理想,恢复古希腊的修辞、文法、历史、法律、医学、天文、数学等知识体系,当时都用“哲学”(Philosophia)
经过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运动”,到了十九世纪,欧洲“科学”已经建构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主张严格的学科分工,学术研究越来越具体,学术培训也越来越专业,改变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全人教育。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开始分裂。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导致原属“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和专门的学问。文、理分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必须的。文理分科,仍然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术界的主流。
在1923年的“理科”(科学)昌明时代,苏柯仁、福开森兼顾“文科”(艺术),在中国办一份“文理杂志”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
《中国杂志》一开始有点像综合性大学的学报,文理科合刊。《中国杂志》倾向于理科,侧重生物、地质、地理学专业,但总体上还算平衡。强调文理分科,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明清以来,自耶稣会士利玛窦以降,他们在中国传播的欧洲知识,大多是关于天文、地理、历法、声光化电。他们尽了很大努力来传播的神学、哲学,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汉学家”们传扬的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得到了赞扬。这样,凡对中华文明有所了解的学者,包括中国自己的很多学者,自然就有了比较,认为“西学”是“重理轻文”,“中学”是“重文轻理”。清末民初一般闭目塞听的腐儒也渐渐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的道德文章世界第一,声、光、化、电等“奇技淫巧”就不妨让于“西学”,他们坚持的“中学”多半就是固步自封的原教旨主义。和这些“腐儒”相比,《中国杂志》的中华文化理念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框架。这些外侨学者天然具有20世纪的世界眼光,他们主张的文理平衡,中西并重,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格局。
上海生长: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信息
我们把《中国杂志》看做是一份在上海编辑、发行的中国杂志,同时又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杂志。在上海本埠(local)、中华民族(national)和跨国全球(global)这三层关系中,《中国杂志》呈现出一个本土和全球直接联系起来的特征,即更加注重Local和Global。《中国杂志》的科研和时事内容以上海为主,中国为辅;同时,编辑部的视野、观点、方法是以二十世纪国际社会兴起的科学、进步、理性、人道、和平等原则,这些又和当时中国内地流行的传统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等社会原理格格不入。《中国杂志》是一份典型的十九、二十世纪通商口岸进步杂志,他受到城市读者的欢迎,也在国际社会获得赞誉,但在一般的内地民众和传统文人中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杂志》的national的层面上影响最小,他在local和global的层面上影响较大。或者更加简单一点地说:《中国杂志》是一份“Glocal”——全球本土化的杂志。
《中国杂志》鼓励上海本地的科学研究,是上海城市研究的一个先驱。
《中国杂志》固然是一份以“上海客”为身份的侨民刊物,但它并不狭隘地只以租界外侨事业为骄傲。相反,它也有浓烈的“上海人”认同,对华人在租界内外取得的成就也表示欣赏和赞叹。对于华人建造的摩天大楼,以及其他市政成就,《中国杂志》同样视为“大上海”的共同成就,一并给予热情的报道。上海的华人事业成就不亚于西侨,这一点在《中国杂志》上有很多记录。
从1923年到1941年的19年的办刊历程,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杂志》身份认同上的变化。《中国杂志》从初期的一份以英、美侨民为主要作者和读者,在英语世界发行的科学文化杂志,到后期转化为侨民和华人学者共同撰稿,在上海和通商口岸地区的英语读者群体中具有影响的中国(人)的科学文化杂志。以上说法太拗口,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中国杂志》早期是一种“上海客”(Shanghailanders)的侨民身份,后期则是一个“上海人”的地方认同。苏柯仁创办《中国杂志》的时候,他更多强调科学的普世意义,希望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事业做贡献;在苏柯仁辞任主编后作为一位撰稿人期间,《中国杂志》更加社会化,它在本土关怀中取得了地方性的身份认同,有了自己的情感,爱上了“此土此民”,它和华人社会在一起,成为一份属于上海和中国的英文科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