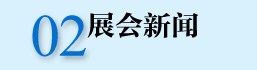一位22岁的实习编辑曾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想下班的想法,每天从办公室地板钻出地面,爬上椅子,把瘫在椅子上的我的心死死缠住。”
对于某些刚入行的新编辑来说,想下班、想“躺平”,可能是日常。而且“我们”实在不能理解,退休后的老编辑们为什么能精力无限,每天各处调研、演讲,还有时间写书?!
为此,本报邀请了一位年轻编辑与国内著名出版人李昕,进行了下面这场对话:
李昕,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现已退休,为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著有《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清华园的记忆》《做书》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只为一事来
Q:我做编辑是因为喜欢文字工作,您是怎么走上编辑道路的呢?
A:我1952年出生,是北京人,出生在清华园,16岁初中毕业后赶上了知青运动,我到吉林省下乡插队,在东北待了整整10年时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1982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30岁,当时就面临着一个职业选择。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在同班同学里条件是比较好的,我当时已经入了党,是班长,那时有人给我们年级60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做了一个排行榜,我在榜上排第二,在我们班里排第一。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是这60个同学里面唯一一个北京人,而那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按名额(用人指标)分配工作,我们这一届有16个北京名额,我被分回北京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在这16个名额里,我选择工作也应该是可以受到优先照顾。
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谈让我留校,说让我教外国文学,一年以后可以送我到美国去留学,全都有承诺,但当时我因为已经30岁了,在北京有个女朋友,而且我父母都近70岁,他们也希望我照顾,所以我决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
北京的单位16个名额里面有公务员,也有新闻、出版、科研、大学等单位的用人指标,怎样选择?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要以“才”“学”“识”来衡量,我觉得我做学问可能有欠缺,“学”不够,不具备比较厚实的学识基础,因为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人家十几岁需要读的书,我是到二十几岁才恶补的,底子不扎实。我注意到我同学里面,比如后来当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陈晋、杨胜群,后来当了文学研究者的於可训、乔以钢等等,他们当时读书就比我多。如果是当作家、当记者的话,我的“才”又怎样,比如写作能力如何?我的同学里有好几个作家,跟他们相比,我的才华也很不够。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上大学以前,在东北一个小城市里,也曾写过诗,自我感觉也算一个小诗人。“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我曾经上过一个中专的中文科,在学校甚至做过诗刊的主编,毕业时学校举办文艺汇演,其中的毕业生集体朗诵的长诗就是我执笔的。但是上大学后,第一个周末,中文系就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也揣着自己的诗去参加了。但是高伐林、王家新他们一上台,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不敢再献丑。于是我当天把衣兜里的诗撕掉了,从那以后,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写诗。
所以在这时我觉得,我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有多年的社会经验,思想比较成熟。于是我选择做文学编辑,因为做这样的编辑需要一种对作品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依赖社会经验和成熟的思想的。这就是“才”“学”“识”中的“识”,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选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学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就把我分配来了。
Q:那时候刚进出版社,是不是得先做校对?
A: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规矩,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以后,面临分配编辑室。和我同来的大学生一共5人,大家都顺利进入了各自理想的编辑部门。轮到我,人事处说不给我分配了,要我留在处里,做政工干部。告诉我,社里要把我作为政工方面的接班人培养。当时的情况,是5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我一个是党员,我一进出版社,就被社里指定为文化部出版局团委委员,负责社里的共青团工作,受到特别的重视。
但是这种安排,绝对不是我本人的理想,我希望自己一生朝着专业方面发展,最终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选择到出版社,如果不是为了当编辑,我就不会来。所以我不能接受人事处长的安排,但是又不敢和她硬顶,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头脑中,个人服从组织的观念是很强的。人事处代表组织,有很高的权威。她是好意,要重用你,你不服从,是不识抬举,肯定要受批评。所以我想,这事情一定得找懂业务的领导帮忙。
Q:后来呢?
A:我看到当时出版社总编辑屠岸面容很和善,是个谦谦君子的模样,于是就想到去求他。其实当时我根本没和他打过交道,他可能还不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到大饭厅吃午饭时,我和他凑到一个桌子上,恳求他给我一次做编辑的机会。我说自己知道,在“人文社”做编辑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但是我希望有一个机会(比如三年时间)尝试一下,如果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做编辑,那么三年以后我就改行做政工干部。屠岸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以后,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了“一言为定”四个字。
这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有动摇有诱惑,但还是爱出版
Q:这样看来,您的编辑之路其实还挺顺利的。
A:我当了编辑以后,确实非常顺利,一年以后,理论组的组长调出去了,我就接了理论组组长。3年以后,编辑部领导班子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副主任,6年以后,1989 年又进行一次编辑部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主任。那一年我36 岁,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十几间出版社范围内,我当时可能是最年轻的正处级业务干部,做编辑做得很顺手,这就给了我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这条编辑的道路。
Q:中间就没有过动摇吗?
A:当然也有过短暂的犹豫。1980年代中期,一些朋友出国留学,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父亲那时是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和美国一些大学有交往,曾经给我联系过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可以兼职教中文。这是极好的条件。但是因为我编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复习外语考托福,最终放弃了。其实今天想来,我没有选择出国,是因为我当时已经真心喜欢编辑这个职业了。
90年代初,出现下海潮。我那时是编辑室主任,我所在的编辑室十几个人中有两人下海,后来都发了大财。其中一位去深圳捞了一桶金,几年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做出版,日子过得很潇洒;另一位后来当了上市公司的老板,不但自己成了亿万富翁,而且还带着100多位曾经与他一起创业的高管致富。他说公司上市前,他和那些高管一个个地签订股权合同,没有一个人当真,都像儿戏一样签了字。结果一上市,所有的高管都傻了,他们全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千万级别以上的富翁。这人是我亲手招到人文社的,与我感情非常好。现在还常常拉我参加聚会。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你当初怎么不带上我一个?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放弃做出版是对的。
到了1993年,下海的人更多了。不下海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也在考虑怎样做生意的问题,好像有一点全民皆商的味道。这时有一个香港地产商,要到国内来发展,先在北京建一个办事处。有人介绍我去做这个办事处主任,说是可以拿高几倍的工资,我也婉拒了。我那时一个月才挣一千元,并没有觉得缺钱花,但是编辑工作很开心,我就知足了。
Q:所以还是爱出版,对吗?
A:我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爱上出版这一行,但其实主要是喜欢做编辑。我喜欢书,对编辑好书有兴趣,乐此不疲。有人说我属于特别有激情的人,一见到好的选题就兴奋,两眼放光。我的确一向如此。这可能和我亲手编了一些好书,受到社会文化界的好评,内心里获得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有关。自己的价值被社会承认,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主管图书发行的副社长退休,社长陈早春提议让我接任。当时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已经5年,兼任社长助理也两三年了,按程序,也该轮到我接班了。但是我因为喜欢编书,不愿意脱离编辑岗位,觉得当副社长就不能编书了,所以又拒绝了陈社长的提议,放弃了一次提拔的机会。当然,如果在今天来看,如果我1994年42岁时就做了副厅局级的行政职务,那么我后来可能会走上仕途,当更大的官。
总要面临很多选择,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Q:其实您的职业生涯中有过很多选择,您后来到三联工作,包括退休返聘,是基于哪些考虑呢?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时,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A:1996年我有机会到香港工作,是公派,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家新闻出版局协商借调的形式,到香港三联书店,一去8年,先做副总编,后来做总编辑,这8年对我的成长和成熟,锻炼很大。2005年初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又面临工作选择。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深圳公司,如果我选择留下,收入会比回北京工作高一些;在北京,也有几家出版社有意请我去担任总编或者社长。而如果我回到北京“三联”,按照我的原级别只能担任副总编(副厅局级),级别比在别处当社长和总编要低一级(我升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是5年以后的事了)。但是我考虑,要编好书,还是“三联”的编辑平台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我选择到北京“三联”,一直做到2014年退休。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有几家国营出版社,也有几家民营出版机构、学术文化单位、还有网络公司希望返聘我,开出的待遇也都不错,有的条件也明显更好。但是商务印书馆找我,表示希望我协助他们做选题策划,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就像我当年从香港回来选择北京“三联”一样,我认为好的出版平台有利于编好书。“商务”是这样的好平台。
Q:回想36年的职业生涯,您有什么遗憾吗?我在职业道路上也会面临各种诱惑,有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坚持下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A:我为了做编辑,36年中经历了多次选择,放弃了很多机会,都是和“升官”“发财”有关的。只要在其中有过一次动摇,一旦改变选择,我的人生就会变为另一种样子。但是我没有左顾右盼,而是一条路走到底,始终坚持当初选定的职业方向,最终也成就了一种比较成功的人生。
虽然官没有做多大,钱没有挣多少,但是我36年来经手策划、责编、复审、终审的图书加在一起,恐怕有两三千本(策划的图书大概有一千多种,其他是我用各种不同形式参与)。这些书不但没有坏书,而且被人称为好书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改造的图书,所以我对自己的编辑人生感到满意,没有什么遗憾。
我不但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还做了一些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而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当然,归根结底,我的幸运在于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出版时代。这40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出版业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代。
第一,我参加出版工作时,正值中国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这时民众对于知识、文化和新思想的渴求突然增大,出版业有了巨大的自由生长空间。
第二,90年代以后,以电脑印刷和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技术使图书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精品化和多媒体化,影响到出版业的发展实现再一次飞跃。我的幸运就在于完整地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时代为我创造了出好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