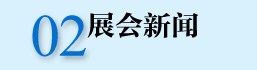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付文军: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摘 要】《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南。国内的《资本论》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得以蓬勃开展起来,一系列译本和研究著述纷纷问世。通过考察发现,国内《资本论》的译介与研究始终是与“时代课题”紧密相联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仁人志士们从事《资本论》译介与研究主要是为了从中找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资本论》的全面传播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要求。改革开放以后,《资本论》的系统传播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相适应的。经过百年的译介和研究历程,国内的《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译介出版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南”。《资本论》之所以有此“功效”,除了这一理论自身具有的科学性以外,还在于中国人民结合“中国”这一最大的实际。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使《资本论》成为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在《资本论》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涉及它的研究与传播问题,只有研究好《资本论》的理论和传播好《资本论》的声音,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资本论》在中国研究与传播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1]的思路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一、1921—1949年:《资本论》的自觉译介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
随着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的迷梦就此被打破,“唯我独尊”的状况也得以改写。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就此遭受列强的百般欺辱,“这极大地激发了有志之士为强国而求知识于西学的潮流”[2]。在见识到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强大威力之后,一批批志士仁人开始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提出“以夷为师”和“中体西用”的号召。“师夷”就要接纳、学习西方“长技”,以达到“制夷”和“胜夷”的目的。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一股“组织学会、建立书局、创办报刊、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介绍西欧资产阶级文化思想”[3]的风潮,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探寻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答案。马克思和《资本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为国人所知晓的。
有记载的资料表明,国民党的部分人士在《资本论》早期传播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中,孙中山是“最早较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4],朱执信、戴季陶和胡汉民等人在《资本论》的翻译、解说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和《资本论》就已出现在各种期刊和著作之中了。马克思和《资本论》最早出现在《万国公报》[5]上。此后,《新民丛报》[6]《译书汇编》[7]《民报》[8]《东方杂志》[9]《新世界》[10]《晨报》[11]和《国民》[12]等杂志也纷纷刊载了介绍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文章。这一时期的《资本论》的译介并不系统,多是个人自发完成的。同时,这一时期《资本论》的传播范围也极其有限,大家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也十分粗浅(甚至存在误释),大多数人只停留在“只知其名”的境况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国内对于《资本论》的需求持续增长,加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国内迅速掀起一阵翻译、介绍和传播《资本论》的浪潮。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率先翻译和介绍了部分《资本论》的入门著作。国人要迅速接受马克思和《资本论》,就要先知晓其人、其事、其思想。虽然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是最佳方式,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要阅读较为晦涩的《资本论》显然不现实。这就需要有通俗易懂的“简易版”“简介版”或“导读版”来达成这一目标。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就迅速编译了“马克思全书”,这其中就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1922年3月15日至5月15日,《今日》杂志先后刊载了《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和《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邝摩汉编译,分别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部分内容)。1922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而编辑整理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其中收录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就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除了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还翻译出版了《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李季译),上海书店组织了“解放丛书”的编译与出版事宜,华兴书局整理出版了《马克斯主义的基础》和“社会科学丛书”,民智书局出版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胡汉民译),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高岛素之的《资本论大纲》(施复亮译)。这些著作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宣传和教育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理论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资本论》的集中翻译和出版也得以实现。早在1924年,郭沫若回国后就拟定了一个五年内译完《资本论》的计划,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他不仅一直坚持研读《资本论》,还在“一九三八年秋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官票宝钞》两文,纠正了中日有名的翻译者对王茂荫这姓名的误解,并解释《资本论》中所说的‘宝钞’是怎么一回事”[13]。1930年3月陈启修(后改名为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开创了中国学者集中翻译并出版《资本论》的先河。潘冬舟(又名潘玉华)则接着陈启修的工作在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册。1932—1936年,王思华(又名王慎明)、侯外庐(又名侯玉枢)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在国际学社出版。1934年5月,吴半农翻译、千家驹校对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在商务印书馆问世。1938年8—9月,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随后,由郭大力独立翻译整理的《〈资本论〉通信集》也在该出版社印发出版。1939年1月,章汉夫和许涤新将俄文版《恩格斯论〈资本论〉》的中译本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刊印。这些译本的问世,对于国人系统地理解《资本论》的思想与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莫大的帮助。
直到《资本论》全译本的问世,国内关于《资本论》的译介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时期国内关于《资本论》的译介和传播也各具特点。
就译介来说,这一时期国内关于《资本论》的译介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①由于《资本论》属于“大部头著作”,加上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此时的《资本论》翻译多采取“节译”(或“摘译”)和“全译”相结合的方式。在战乱时代,由于《资本论》的翻译和出版遭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多重阻力,只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的全译本得以出版。其他面世的则多是“节译本”,或者是“简介版”。②《资本论》及其相关文献的翻译采取了参照原文、借鉴日文译本和俄文译本相结合的方式来完成《资本论》的译介工作。其中,日文文献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理论翻译,凡有日文译本可供参考的,都从中得到不少方便,因为日译的名词、概念的用语大量采用汉字表达”[14]。尤其是经济学的专业词汇,如经济学、经济、生产和资本等都是从日文直译过来的。③这一时段的《资本论》译介以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实施为主,国民党在译介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资本论》著作,还运用了唯物史观来透视中国的诸多问题,使得理论和实践得以结合。
同时,这一时期国内《资本论》的传播也具有两大特点:①就传播形式来说,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口头宣讲(宣传)和集中学习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熟知《资本论》。“据史料记载,周恩来同志就是口头宣传《资本论》的杰出代表。1920年,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工商界和学生集会游行而被捕,在狱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给被捕青年和各界代表讲解马克思学说,其中就包括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15]集中学习则主要是在学社(书社)和学校中进行。毛泽东在长沙组建的文化书社、周恩来在天津筹建的觉悟社和新生社、恽代英在武汉组织的利群书社在宣扬《资本论》的思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达、黄松龄、王思华、侯外庐、施存统及陈启修等人在学校开设了《资本论》的相关课程,[16]他们将翻译、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深入地传播了《资本论》。②就传播途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依托出版社和期刊阵地来呈现《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昆仑书店和北平东亚书局等都纷纷出版发行了《资本论》的各种版本,《晨报》《先驱》《星火》《明日》《新时代》《向导》《觉悟》《革命》《学灯》《政治生活》《思想》和《流沙》等期刊也纷纷以连载、转载和邀稿的形式刊载了《资本论》的解读本和原文。
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传入是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方略的必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论》在中国经历了从著作介绍到翻译片断,再翻译全文,从自发传播到自觉运用,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17]这些译本和介绍性的文字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坚定人们的革命斗志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怀揣救国之志和救民之心的仁人志士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革命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在这时的译介和传播恰好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农民运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改革、民主革命都被实践证实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资本论》的译介和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能够出现在中国人民的视界里,能够用这一理论来解决中国所遭遇的问题,这定然是马克思所乐意看到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既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又要利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资本论》的译介和传播就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环节。经过一代代学人的不断努力,适合中国人阅读的《资本论》的译本先后问世,翻译的水平和质量也逐渐提高。同时,在革命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也利用《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完成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民众革命的积极性,为争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援。
二、1950—1977年:《资本论》的全面传播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一是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二是改造人们的思想以重树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我们开启了学习苏联模式的道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了起来。在随后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热潮”,不仅“机关、部队、工厂等单位都规定了专门的学习时间,制订了学习计划”,学校也设立了“政治理论课”[18]。在此背景之下,迅速、广泛、大量地整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为了迅速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组建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后在1953年合并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集中力量编译经典文献。同时,以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的人民出版社也在1950年底成立。这有效地推动了国内《资本论》的翻译和传播。
(一)《资本论》的五种传播形式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国内的《资本论》的传播主要有五种形式。
1.再版之前的《资本论》译本
为了迅速传播和学习《资本论》的相关理论,在“新译本”未出版前,还需借助“旧译本”来完成任务。为此,《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雇佣劳动与资本》(沈志远译)、《剩余价值理论》(郭大力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郭大力译)、《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何思敬译)、《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和《价值价格与利润》(王学文、何锡麟译)等译本纷纷被重新印刷出版。其中,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全译本在1950年便重印了一万部,“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天津、济南、西安、长沙、开封、大连、哈尔滨、重庆、汉口等大城市发行”[19]。
2.重新翻译并出版《资本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同志根据德文版第23、24、25卷,并参照了俄文版和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翻译、整理了《资本论》,并将《资本论》列为第23—26卷(共四卷六册,其中,《资本论》第1—3卷分别对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剩余价值理论》则分三册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三册之中)。1972年9月至1974年12月,四卷六册的《资本论》在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每卷均发行十三万册”并出版了“单行本”。[20]
3.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于《资本论》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的理论内涵,更好地了解《资本论》在国际上的研究状况,国内的学者也纷纷致力于翻译国外有关《资本论》研究的文献。苏联学者帕尔卓夫的《论〈资本论〉的结构》(余学本译)、列昂节夫的《马克思资本论和现代》(季谦译)和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等文献被迅速翻译出来。日本学者山川均的《资本论大纲》(傅于琛译)和长谷部文雄等的《〈资本论〉索引》(陈可焜译)等文献也相继出版。这些文献的翻译和出版,为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提供了便利。
4.出版了《资本论》的“解读本”和相应的辅导材料
基于国内的实际情况,编纂一些适合中国人阅读、激发中国人兴趣的辅助材料也成为当务之急。王思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并编纂了《〈资本论〉解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志远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孟氧编写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发行打印稿,1954年),郭大力完成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复印稿,1957年),王亚南出版了《〈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这些资料配合《资本论》的原文,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阅读和传播这一理论。
5.研究性的论文也纷纷出炉
为了适应特殊的时代要求,此时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生产方式”和“阶级专政”展开的,王亚南、吴传启、孟氧、王学文、汤在新、沈佩林、许涤新、孙冶方、蒋学模、骆耕漠、熊映梧和刘诗白等是研究的主力,《教学与研究》、《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世界经济文汇》、《读书月报》(后更名为《读书》)、《中国经济问题》、《学术月刊》、《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学术研究》和《经济学动态》是主要的理论阵地。
(二)《资本论》的传播与研究特色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我国的《资本论》翻译、研究和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与研究特色。
1.翻译和研究相结合
对于《资本论》而言,翻译和研究不是孤立的两个程序或环节,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翻译可以更好地促成研究,研究则能使得翻译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资本论》的翻译过程中,这些译者不仅是《资本论》研究的权威,还是各个机构讲授《资本论》的专家。正是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推动下,《资本论》的思想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散布开来,并为中国人民所接纳。
2.文本译介和应用研究相结合
《资本论》的文本翻译是要满足中国发展需要的,单纯的文本翻译虽然能够起到传播文明、扩大影响的作用,但毕竟影响有限。文本译介必须要观照现实,必须要以回应时代之问为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社会主义改造该如何展开、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落实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因此,此时的《资本论》译介、研究不再拘泥于纯粹的文本研究和枯燥的理论分析,而是开始关注并指导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在化解现实问题中,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资本论》的理论魅力。
3.普及性的宣传和精细化的研究相结合
由于受众不同,《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策略也各不相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来有条不紊地传授《资本论》的思想显然不切实际,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围绕一些有关《资本论》的“提要”和“提纲”来宣讲《资本论》倒是可行之法。当然,对于知识层次较高的专业人员而言,他们又需要精细化的研究和深层次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并用《资本论》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这一时期的《资本论》传播和研究的环境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状况有着天壤之别,《资本论》的译介、研究和宣传工作也从“地下”转为“地上”。这一工作不仅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还深受民众的爱戴和追捧。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遭遇了挫折,但从总体上来说此时的《资本论》研究与传播取得了一个质的飞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实现了《资本论》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对接,即运用《资本论》的基础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恢复生产、探索工业化道路的目标。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民学习《资本论》的风潮。“机关、部队、学校等都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进行马列原著学习。各高校各专业都把《资本论》列为必读书,财经类院系都开设《资本论》专门课程。”[21]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资本论》的传播事业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在国家的推动下,《资本论》不仅进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虽然也有《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甚嚣尘上,但并没有改变全社会日益接受《资本论》的大趋势,尤其是《资本论》已经融入到高校、科研院所等教育教学体系中,并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为《资本论》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保障”[22]。
三、1979年至今:《资本论》的系统传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
在1978年之后,《资本论》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的有四个重要事件。一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号召人们要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思想领域的极端状况和一潭死水毫无活力的情势也得到根本性改善;二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这就需要深入钻研《资本论》的基础理论以实现对现实问题的答疑解惑;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的启动。2004年4月27日,党中央启动了“马工程”,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人才;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迎来了大好时机。《资本论》的传播和研究自此迎来了“暖春”。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重新整理、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资本论》,也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单行本。就《资本论》的翻译来说,此时的译本主要参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该版原则上把已知的作者写成的全部文献用原文按照原貌发表。所谓用原文发表,就是用作者写作时或发表时使用的文字刊印,不作翻译;所谓按原貌发表,就是所有字形字体字号、标点符号、勾画线条、段落划分、篇章结构,均遵从作为底本的手稿或刊印稿,不作变动,不进行编排”[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不仅收录了《资本论》三卷,还将“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1867—1882年手稿”收录其中。《资本论》三卷分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第44、45、46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第5、6、7卷。《〈资本论〉节选本》在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2017年再版。《资本论》三卷的单行本也在2004年出版,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再版。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阅读《资本论》的需要,“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以中央编译局中文版为底本,把《资本论》翻译为各少数民族语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蒙古文、朝鲜文《〈资本论〉(节选本)》。1989—2002年,出版蒙古文《资本论》3卷和朝鲜文《资本论》第1、2卷。2007—2015年,出版蒙古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资本论》3卷和藏文、维吾尔文《资本论》第1、2卷”[24]。
就《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来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一方面,学术团体和学习团队的推动、学术基金和学术阵地的支持是促进《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1980年,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立(陶大镛为名誉会长);1981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许涤新任首任会长);1983年,在刘诗白先生的倡议下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立;1986年,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卫兴华任首任会长)成立并在厦门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2019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更名)成立(程恩富任会长)。这些学术团体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征集学术论文、组织学术交流和出版学术论文集扩大了《资本论》的影响力,各《资本论》研究个体也通过会议交流而汇聚成研究的合力。[25]不仅如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持续地资助着《资本论》的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纵横》《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和《学习与探索》等是国内《资本论》研究者发声的平台,它们是国内《资本论》研究主要的理论阵地。[26]当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学习时报》和各级报刊都为《资本论》的宣传提供了平台和渠道。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经济学的交锋中,《资本论》的生命力得以凸显。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普及严重地冲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实际工作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了,并一度陷入“失语”“失踪”和“失声”的尴尬境地。纵使《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一度陷入了“寒冬”,但一代代研究者和传播者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研究阵地和宣传平台。就《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阵容来说,各高校(包括科研院所)的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学院(或哲学系)是研究和传播的主力。在《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过程中,经济学界厥功至伟,哲学界也功不可没。《资本论》就是一个理论宝库,其间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思想。学界和宣传部门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了对《资本论》的解读和宣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和传播模式。在《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过程中,经济学界率先展开了对《资本论》的经济学解读,形成了以许涤新、卫兴华、刘国光、刘诗白、陈征、胡钧、洪远朋、李建平、许兴亚、简新华、逄锦聚、程恩富、洪银兴、顾海良、刘灿、林岗、裴长洪、高培勇、丁任重、丁堡骏、邱海平、张宇、周文、聂锦芳、孟捷、余斌、刘凤义、张旭、谢富胜和徐洋为代表的“衔接有序的研究梯队”。改革开放之后,哲学界以经典文本为基础,“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挖掘经典文本内蕴的思想资源、重新激发其思想活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伟力”[27],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条研究路径[28]。就《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内容来看,学者们纷纷以“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积累)”“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经济危机”和“新时代”等为主题展开了对《资本论》的精细化研究,并在学术探索和理论宣传中展开了对《资本论》的方法、对象、起点和性质的论辩。[29]围绕《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学界也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成果。如《〈资本论〉难句解》(刘诗白主编)、《〈资本论〉解说》(陈征著)、《〈资本论〉脉络》(张熏华著)、《〈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何炼成等著)和《通俗〈资本论〉》(洪远朋著)等是极具代表性的解读性著作,《〈资本论〉研究》(许涤新著)、《〈资本论〉的逻辑》(田光著)和《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孙承叔、王东著)等是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性专著。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资本论》凭借其科学的方法和人民的立场而成为中国人民用来讨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主要工具。虽然在与西方经济学的交锋中一度处于颓势,但《资本论》的理论魅力——“从理想的价值状态出发批判现实社会并超越现存状况”[30]——预示着它必然会在新时代里持续发光发热。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资本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法宝。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资本论》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积极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法和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结语
随着《资本论》传入中国,将这一“舶来品”变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成了每一位《资本论》的研究者和传播者的重要任务。在《资本论》研究与传播的百年历史中,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华丽转身,经过不断努力,我们正迈入一个“强起来”的时代。在“强起来”的时代里,继续推进《资本论》的中国化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一方面,我们既要在回顾历史中总结经验,又要在比较鉴别中坚定理论自信。回顾《资本论》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的历史,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总结《资本论》研究和传播中的经验教训,以供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和传播中少走弯路,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并开辟《资本论》中国化的新境界。同时,《资本论》的中国化又必须要善用历史资源,一代代学人前辈留下的论著都是我们必须善用的“历史资源”,一代代学人在翻译、研究和传播《资本论》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历史教材”。当然,我们还必须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和论辩中揭穿他们见物不见人、重效益而过分强调资源配置技术的真面目,继而坚定信心——既要坚定对《资本论》的理论自信,又要增强《资本论》研究的信心。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实践中持续推进《资本论》的中国化。西方经济学无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现象”。《资本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我们必须在实践中着力推进《资本论》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对接。尤其是在新时代,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做好扶贫工作,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必须要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新时代的《资本论》研习者要“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充分吮吸“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31],要充分利用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32],继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33]。简单地说,在《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中要做到立足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解释中国道路、回应中国问题,以此来产出一批批立足国情、着眼长远、放眼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高质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8.
[2]杨春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J].经济学动态,2019(10):11-23.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4]张远航.经典追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899—194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344.
[5]《万国公报》在1899年第121和123期所连载的《大同学》(原名《社会的进化》,颉德著,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提到了马克思并对《资本论》的一些片段有简要的介绍。在第一章“今世景象”中,“英人马克思”被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4)。
[6]《新民丛报》分别在1902年第18号、1903年第40—43号刊发了梁启超的两篇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和《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文中提到了“麦喀士”(即马克思)。
[7]《译书汇编》在1903年第11期刊发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中介绍了“马克司”(马克思),并附录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的书目。
[8]《民报》在1905年第2号和1906年第12号分别刊发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朱执信著)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胡汉民著),着力介绍了“马尔克/马尔喀”与“嫣及尔/烟格尔士”(马克思与恩格斯)。
[9]《东方杂志》在1911年第6期所刊发的《社会主义与政策》一文简单地介绍了楷尔•麦克(卡尔•马克思)与《资本论》。
[10]《新世界》在1912年第2期刊载了蛰伸(朱执信)翻译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专辟一节介绍“资本论之概略”。
[11]《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的专栏,并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连载了《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在1919年6月至11月则连续刊载了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12]《国民》在1920年第2卷第3号发表了《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费觉天译),这篇文献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首个中译本。
[13][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9,73.
[15][17]聂锦芳,彭宏伟.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4,46.
[16]雍桂良.《资本论》的写作与传播[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226.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7.
[19]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第8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685.
[20]雍桂良.《资本论》的写作与传播[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229.
[21]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J].东南学术,2002(1):4-15.
[22]聂锦芳,彭宏伟.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7.
[23]徐洋.《资本论》及其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情况分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3):63-75.
[24]徐洋,林芳芳.《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2):9-21.
[25]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已成功举办了21届,其主要工作为:沟通和协调有关方面的《资本论》研究计划和活动,组织和推动学术交流和资料交流;组织各种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编辑出版《当代经济研究》等学术性刊物;开展《资本论》的宣传工作;组织力量做好国外学术情报工作,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也举办了17届会议,并在师范类高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汇聚了师范类院校的《资本论》研究合力。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从成立起每年都坚持举办年会,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36届年会,并积极组织出版了《中国<资本论>年刊》(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也陆续举办了18届会议,在综合性高校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也召开了13届年会,并召开多次专题理论研讨会。在新任会长程恩富先生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业务培训、书刊编辑、国际会议、咨询服务等活动。
[26]付文军,谭兴林.中国《资本论》研究70年:1949—2019[J].经济学家,2020(1):13-23.
[27]王海锋.视角转换与激发经典文本的思想活力——基于《资本论》研究史的检视[J].求索,2021(1):20-29.
[28]第一条研究路径是借助于“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遵循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和模式来研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理论,形成了历史现象学(以张一兵为主要代表)、生产关系现象学(以王峰明为主要代表)、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以孙正聿为主要代表)和资本现象学(以白刚为主要代表)四种现象学的解读模式;第二条是文本学的解释路径(以聂锦芳为主要代表),这一解读模式主要围绕着文献还原与版本考证、文本研究与概念梳理、思想阐释与理论建构而展开;第三条是历史化的解读路径(以孙承叔为主要代表),这一诠释路径抓住了“现代社会”这一关键,并对其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继而科学地剖析了它的内部结构、运行机理和历史趋向(具体参见:付文军.《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进路与理论自觉[J].天府新论,2020(1):24-34)。
[29]付文军,谭兴林.中国《资本论》研究70年:1949—2019[J].经济学家,2020(1):13-23.
[30]刘同舫.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J].中国社会科学,2020(9):4-22.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9.
[32][33]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