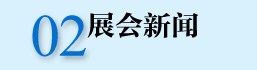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赵鹏: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鲁迅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对儿童读物带着强烈的启蒙意识,其中既期待儿童读物发挥出“立人”的实效,又不满于儿童读物的出版状态,既反对旧文化的保守和压抑,又警惕新文化的功利和游离,由此构成了鲁迅对儿童读物的热切又犹疑的矛盾态度,梳理其思想流变和精神实践的过程,能更深入理解启蒙思潮与近代儿童读物的关系,也有助于讨论儿童读物的出版初衷。
【关键词】儿童读物;鲁迅;启蒙
儿童读物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源于科举制的废除、启蒙思潮下传统教育理念的变革、现代印刷技术的运用,以及书刊零售方式的形成。鲁迅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文学社团,推动书刊出版,其中对儿童读物的出版现状,既有热切的期待和认真的探究,又有严厉的批评和理性的借鉴,纵观鲁迅对儿童读物评论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既牵动了他对社会启蒙潮流进行反思,又关系到他的创作和翻译走向风格变化的特殊领域,他在其间的态度既显示出启蒙者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又在启蒙与出版之间保持理性追求。
一、鲁迅的启蒙理想:从孩子的成长出发
近代社会变革打破了旧社会的秩序,新式的儿童读物在启蒙思潮中逐步发展起来。以1909年孙毓修主编出版的《童话》为例,以“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为依托,力图形成“与庄严之教科书相对”的新式儿童读物,[1]丛书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分为两编,共77种,获得了巨大社会影响。儿童读物从五四前后开始出现了小说、童话、儿歌等多种类型,内容上涵盖社会、公民、科学、美术、劳作、算数、卫生、谜语、自然等。同时,一些投身启蒙实践的文学和出版工作者,积极采集民间故事和传说,整理童话、童谣、儿歌,并展开相关的研究,如周作人关于儿童的研究,叶圣陶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童话,写了《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多多为儿童创作》等文章呼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类文章还有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儿童读物的开拓。
在这一研究、创作和出版的热潮中,鲁迅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早在任职教育部时,他就开始关注儿童问题。这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也与周作人相关,1914年1月至7月,周作人在绍兴收集儿歌,并组织艺术展活动,将所翻译的儿童研究文章寄给鲁迅修改,两人都关注儿童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览。1913年至1915年,鲁迅负责协调组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活动,其间翻译了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和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这几篇文章主要探讨孩子对艺术欣赏习惯和心理机制问题,[2]从儿童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出发,成为鲁迅关注儿童的起点。
从儿童的特点出发,鲁迅作品中的孩子不是听话顺从的状态,鲁迅着意表现的是孩子的活泼和“动”的一面。1913年他发表了《怀旧》,开篇描写了一个淘气的顽童,希望秃先生生病甚至死去,自己就不用上学了。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中继续运用了童趣的手法,其中《他们的花园》描述了一个孩子想得到一朵百合花的焦急心情,体现出对儿童心理和行为的深入把握。这是鲁迅对儿童心理的尊重,也是启蒙思想的创作实践。需要注意的是,他所立足的并不是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是从孩子本身出发显示其活泼的一面,这就构成了他与同时代启蒙者思考角度的不同之处。
1922年,鸳鸯蝴蝶派胡怀琛发表儿童诗歌:“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就此,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儿歌的“反动”》作为批判:“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3]
鲁迅批评的着眼点是成人对儿童心理揣摩的庸俗倾向,半个月亮可能被人“偷”了,失去了《玉台新咏》中“破镜飞上天”的天马行空,看似是对童趣的戏仿,实际正说明成人对孩子心理关注的缺失,以革新的姿态去启蒙,所表达的依然是传统伦理观念,需要的是对儿童真正的关注。
这让人不禁想到,在《故乡》中“我”所渴望的是闰土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长妈妈讲的赤练蛇的故事,还有“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以及用荆川纸所描《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这些回忆既是鲁迅不断回味童年的滋味,从中寻找孩子主体的真实感受,也是在回味自己的好奇心,像双喜、阿发那样爽朗的孩子,甚至像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六斤,这些孩子才是鲁迅希望的有鲜活生命力的精神底色。
在启蒙思潮中,社会认知中依然保持着传统观念,以成人的视角去揣测孩子,对于鲁迅而言,用现代的意识解放成人的思想,成人接受启蒙的意义和方向,比起“救救孩子”更为迫切。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提出了父亲的觉醒问题,实际是将社会变革的主体赋予成人,也就是将“救救孩子”的拯救者角色赋予了父亲,这意味着父亲和成人社会须关注孩子的审美趣味与心理需求,成人才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不是其他启蒙者所热衷的将希望和理想寄予未来或下一代,将孩子看成是不完全的人时,并不是真正的启蒙意识,成人对儿童的态度延续的依然是旧的伦理观念和训教方式。
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就能理解鲁迅在回复许寿裳的书信中对儿童读物的评价:“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4]鲁迅在这里主要是批评儿童读物的缺乏,但也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旧式的儿童读物不好,而文学革命后的儿童读物的走向,启蒙者也需要反思。
二、实践反思:鲁迅对早期儿童读物的质疑与批判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启蒙思想的传播,鲁迅对儿童读物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和现实的双重批判。在《二十四孝图》的开篇,鲁迅以文学革命发生之后的改变来看,在“供给孩子的书籍”上,与其他国家对比,虽然数量上少,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就如“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5]。他回忆自己幼时受到的孝道伦理的训教,质疑的是文学革命以来启蒙所应产生的成效,儿童读物的内容和方式依然是“听话”和“从命”,数量的丰富并没有带来思想上的变化。
从当时出版行业的情况看,儿童读物经过五四启蒙思潮的推动,在20年代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问题。一是内容过于庞杂,二是功利化的介入。从五四前后“儿童丛书”“儿童文学丛书”等图书出版开始,专门给孩子的刊物也开始创办,如《少年杂志》(1911年创刊)和《学生月刊》《中华童子军》《中华儿童画报》(1914年创刊),仅1922年一年就创刊了著名的《儿童世界》《小朋友》《儿童画报》等。从1935年出版的作为广告手册的《生活全国总书目》中可以看到,其分册《全国少年儿童书目》所汇集的儿童读物有3000多种,占总书目的近七分之一。从分类上看已经有普通读物、语文、社会、公民等10个大类,132个小类。[6]
到30年代,参与儿童读物出版的出版机构有50家以上,图书从“丛书模式”跃升为“文库模式”,一套文库就包含达几百种图书,内容翻新出奇,品种不断增多,如《幼童文库》约200种,《小学生文库》约500种,《小朋友文库》约450种,《小学各科副课本》300册等,[7]内容结构向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看齐的同时,儿童读物与市场经济利益达成了某种默契,追求种类和数量的飞跃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鲁迅在1934年对儿童读物提出更尖锐的批判,“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这是对社会上出现儿童读物的商业倾向的质疑,同时他反思儿童读物的内容,“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8],所揭示的问题是儿童读物已经不是启蒙新知、增智启慧的读物,这一严厉的口吻中包含着对启蒙以来儿童读物出版方向和追求利益的批评。
从儿童读物反观教育方式的变化,鲁迅将问题根源归结为“滥调”的重复。1933年他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提出新式的教育中实际依然“教着做古文的滥调”,一面是教育变革中的儿童读物的混乱,另一面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未变的教条。[9]在《难行和不信》一文中他批评对孩子的教条教育方式,反对成人以《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中的故事进行说教。回忆自己幼时所看的图书《日用杂字》,他对比儿童读物《看图识字》,感到色彩恶浊、画面死板,内容与实物不同,他感叹作者根本无力创作,实际还是对启蒙实效的否定。直至1936年,他在《难答的问题》和《立此存照(七)》中批判以儿童读物为媒介的训教,他认为“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10],旧的说教方式并没有因为启蒙发生变化,反而以新的媒介生成奴性教化的新形式。
这些言辞和批评中,鲁迅显现出一种游离和矛盾的状态,既区别于同时代启蒙者的热情呼吁,又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不过,他的角度依然是从儿童本身出发,是对生活和媒介中的儿童形象的追问。1933年《上海的儿童》中提到中国也有给儿童看的画本了,但眼之所及,“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他反思问题所在,经过了启蒙和变革,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生活状态,“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是对于孩子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启蒙不够彻底,对儿童的思想意识还保留着过去的观念,在家庭中给予孩子的方式要么是任其跋扈,要么是冷遇呵斥,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11],在儿童报刊中对比儿童形象,揣摩从传统到现代的“儿童相”[12],他所质疑的是出版物中儿童的形象,也在困惑社会启蒙的走向和获得的成效。
这些反思和批判,实际也在提醒人们回归启蒙的初衷,回到“人”的解放这一初衷,儿童也需要被视为“人”的个体。在《看图识字》中鲁迅认为孩子是“敬服”的,成人早已“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而将孩子“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13],这样态度下出版的儿童读物并不理想;作为“人”的启蒙,鲁迅给予儿童的态度是“敬服”,对生命个体的成长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局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制约,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强调儿童作为“人”的意义。
三、借鉴异域:鲁迅翻译实践中的思想抉择与价值探寻
近代启蒙思想深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就儿童读物而言,鲁迅的吸收和接纳也是有选择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也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皇帝的新衣》和《安乐王子》,如今这些被人们视为儿童读物,而就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初衷来说,这些素材只是作为开启民智的参照文本,并非专门为儿童群体所翻译,这一点在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客观地说,爱罗先珂的童话与当下的童话也有一定的区别,他并不是针对儿童的需要进行创作,只是用童话的文学样式,表现的是对社会启蒙的思考。鲁迅所看重的是爱罗先珂童话中的“童心”,“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14]。他于1922年出版了《爱罗先珂童话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又于1923年出版了《桃色的云》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其副题为“俄国V.爱罗先珂作童话剧”,他对社会的启蒙意识与爱罗先珂的童话表达方式有着精神层面的对话关系[15]。
鲁迅借用了别人的看法对爱罗先珂童话进行评价,“有人说,他的作品给孩子看太认真,给成人看太不认真,这或者也是的”,他理解爱罗先珂的作品具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16],以童话和象征的方式继续推动启蒙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对强权的愤怒,促使人们的觉醒。不过爱罗先珂遭受的冷遇,让鲁迅尤感悲哀,这也使鲁迅从革命的热情中冷静下来,以更为理性的眼光看待人性的复杂和改变的艰难。
可以看到,《狭的笼》《池边》《鱼的悲哀》这些童话中,动物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在象征层面所折射的问题更具穿透性,生命的挣扎和觉醒才是鲁迅所关注的问题,童话这一内容载体并不是儿童专有,这也体现出鲁迅对儿童读物的启蒙定位和现代内涵。
由此,就能理解鲁迅在随后的翻译中,虽然作品中角色是孩子,但鲁迅将孩子首先视为人,以人的角度看个体生命的经历,孩子的状态只是他成长的一部分。如他对《小约翰》的评价是“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主人公的奇幻经历是一个孩子的角度,但从象征意义上看,就是一个人从童年出发走向现实社会的历程,在知识、科学、命运和苦痛的选择中看到“人性的矛盾”和“祸福纠缠的悲欢”[17],结尾所表现的是成长后勇敢地面对黑暗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他对儿童读物的定位与爱罗先珂类似,并不限定于儿童这一群体,但又与孩子相关,就是从“人”的角度看生命的过程。
再如《表》中,流浪儿彼蒂加为了偷一块金表被送进了少年教养院,在不断尝试逃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与同伴的遭遇,领悟了生活和生命的方向,这一成长让他不再逃离现实,而开始认真面对自己的选择。与《小约翰》一样,鲁迅所看重的是生命个体的自我挣扎和成长,是在体会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他人中形成的对自我的确认,从而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和抗争的勇气。
李长之认为鲁迅所翻译的童话中,“只有《表》是真正为了现代的儿童”[18],鲁迅在《表》的《译者的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认为,“现代的新的孩子”需要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鲁迅提出这样的儿童读物需要“有益”和“有味”,内容簇新,富有滋养,给人益处,有味有趣,这应该是鲁迅对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物的基本态度。
鲁迅曾评价中国作家所创作的童话,对比国外的童话,他认为“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重要的是他同时提出,社会上所流行的儿童读物,“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依然是旧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传诵,故事里依然是“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些故事无法与现代社会的新的观念相匹配,“那么‘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比中国和外国的童话中,鲁迅看到了儿童读物创作的差距,这一差距依然并不是童话素材的问题,而是创作的意识问题,需要“新的”,需要“有益”和“有味”[19]。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篇章中,他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弟子规》《鉴略》《幼学琼林》《二十四孝图》等旧式的儿童读物持否定态度,但如何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物,在他而言也并不是简单的问题。
1925年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儿童读物”有一点更为清晰的讨论。在分析《列仙传》和《神仙传》时,他提问:“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也有人会认为,“正合儿童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20]
从这里可以看出,就古代神话而言,作为儿童读物的素材,鲁迅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否定其旧,而重在社会有良好的教育和科学的认知。也就是说,鲁迅对儿童读物的评价并不以新旧作为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现代启蒙的意识,从“立人”的思想出发,对旧的材料重新认识,需要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需要认真研究儿童和儿童读物,才是成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亦如他在《看图识字》中所说,“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这不仅是对儿童的尊重,也是对儿童读物和出版本身的尊重。
四、唤起初心:儿童出版的启蒙意义与“立人”追求
从1920年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开始,这一文学的命名在儿童读物方面实际构成了“儿童”被发现和儿童读物的出版领域。同时代启蒙者都在呼吁对儿童这一群体的重视,鲁迅显现出冷静而理性的反思态度,甚至与周作人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周作人更多显现出教育和实用的倾向,鲁迅则多以旁观的角度看待儿童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他所值守的依然是“人”的启蒙,而不是将启蒙的希望放在儿童这一群体的身上。
在诸多书信中,鲁迅坦言自己并不专门关注儿童读物。1936年3月给杨晋豪的信中提到自己“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曾有一两本童话,那是为了插画,买来玩玩的”[21],4月在给颜黎民的两次回信中提到“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22],“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23],信中希望人们在读书时不局限于文学,还需要多读通俗的科学类图书。向前溯源,还会看到鲁迅1929年致许寿裳的信中直言,“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24],1933年写信向许寿裳寻求“儿童心理”方面的书,并认为“大约此种书出版本不多,又系冷色,必留意广告而特令寄取”[25]。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儿童这一群体虽然有关注,却并不局限于社会主流的儿童观认识,作为一个群体心理和语言行为的考察,他并不是按照划定的标准去看待儿童本身,事实上也能看到鲁迅所创作和翻译的相关儿童的内容中,并不是专门为儿童群体所作。
那么,回到问题本源,可以说,儿童在鲁迅的眼里首先是一个生命个体,是他的“立人”思想的一部分,儿童读物也本来是让孩子获得精神解放的出版物形式。作为启蒙的一部分,鲁迅给予儿童读物的态度是敬畏,从儿童本身的角度出发,对这个生命个体的成长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局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制约,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创造具有“立人”意义的儿童读物。在具体的儿童读物实践中,他回归儿童的本性,鲁迅从自己童年的记忆出发,以《朝花夕拾》的“带露折花”,对传统文化中儿童读物的重新评价,对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筛选,实际构成了他对儿童读物的基本评价标准:一是从生命个体的感受出发;二是符合启蒙思潮的现代指向;三是抛弃旧的训教模式,追求有精神滋养和有趣味的,能让孩子获得新知的内容。这些特征也成为他对社会启蒙获得实效的期望。
回归启蒙初衷,儿童读物本来是因社会变革转型和文化启蒙而蓬勃兴起的出版领域,这一领域既是现代意识下对儿童这一群体的重新发现,也是关注儿童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促进社会文明的更替和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年龄范围的出版物,如果这一领域被社会商业和政治话语所包围,实际上也意味着近代社会启蒙思想的退潮和保守思维的复位,这不仅是儿童读物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这就需要回到启蒙的初心,需要重新认识儿童读物的本源,回到“人”的发现和现代的呼唤。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对于孩子这一群体的命运,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父亲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6],这是对父亲的期望,也是对成人世界的期望,作为孩子的哺育者,在社会转型中既要清醒于批判和重构的文化是什么,也要勇于承担旧的文化和伦理重担,给孩子成长的机会。
儿童读物的出版者,作为孩子精神食粮的提供者,与父亲角色一样,在社会变革中也需要转变自身的态度,需要从孩子这一生命个体的成长出发,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复杂关系,既能让孩子走出旧伦理观念的影响,重视生命个体价值和意义,又不被商业利益和社会舆论所影响,从鲁迅对儿童读物的评价和实践中衡量取舍,在编辑出版中形成新的、有益、有味的儿童读物,秉持现代意识和启蒙初衷,面对儿童读物的思路定位、数量的增长、域外读物的冲击,即便对于当下的出版而言,也可谓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王泉根.《童话》序.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M].太原:希望出版社,2016:44.
[2]姜彩燕.从“立人”到“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之好奇心》等论文的翻译及其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2009(8):35-41.
[3]鲁迅.儿歌的“反动”.热风[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1-412.
[4]鲁迅.190116致许寿裳.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9.
[5]鲁迅.《二十四孝图》.朝花夕拾[M]//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8-259.
[6]平心.生活全国总书目[M].上海:生活书店,1935:1-106.
[7]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499.
[8]鲁迅.新秋杂识.准风月谈[M]//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7.
[9]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准风月谈[M]//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1.
[10]鲁迅.难答的问题.且介亭附集[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89.
[11]鲁迅.上海的儿童.南腔北调集[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80-581.
[12]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26.
[13]鲁迅.看图识字.且介亭杂文[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38.
[14]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译文序跋集[M]//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4.
[15]孟庆澍.铁屋中的“放火者”——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186-191.
[16]鲁迅.《池边》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M]//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17]鲁迅.《小约翰》引言.译文序跋集[M]//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1-282.
[18]李长之.后记.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79.
[19]鲁迅.《表》译者的话.译文序跋集[M]//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6-437.
[20]鲁迅.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5.
[21]鲁迅.360311致杨晋豪.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
[22]鲁迅.360415致颜黎民.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7.
[23]鲁迅.360402致颜黎民.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6.
[24]鲁迅.290323致许寿裳.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25]鲁迅.330302致许寿裳.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7.
[26]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