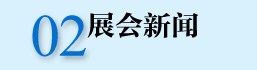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摘 要】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无论是自然权利说还是功利主义说,都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不可识别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传统规制手段均将归于失灵。从不可识别性这一客观前提出发,探索人工智能创造物与人类作品分流保护的制度,如提高并设置不同的独创性标准,构建分层保护的著作权制度等,以构成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法律问题的未来可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不可识别性;分流保护
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界便对自助式照相机所摄照片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展开了讨论。美国也在同一时期成立了CONTU委员会,针对计算机创造物的著作权问题发布了专门的研究报告,并允许编程者对计算机软件创作的文字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1]然而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始终未对此问题做出明确表态。斗转星移,作为近半个世纪科技突飞猛进的一大成果,人工智能创造物迎来了大爆发。它的典型代表包括由写稿机器人自动生成的财经新闻和体育新闻,由音乐创作程序和写作程序生成的乐谱、小说甚至诗歌,由进化算法软件生成的图片,等等。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也因此重新成为讨论热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计算机创造物”阶段:将人工智能当作人类创作的工具,进而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物与普通作品并无二致—最多只需要变通性地运用“职务作品”“法人作品”之类的现有规定,界定其权利归属即可。[2]这种“工具论”的预设前提一方面限制了讨论的深度,将问题人为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也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不符,有闭门造车之嫌。本文所讨论的人工智能创造物,是指由人工智能独立生成的作品;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的操作者仅从事非创造性的活动,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也无从预测该创造物的产生,无法重复产生该创造物。换言之,人工智能创造物中的人类贡献微乎其微,其主要的贡献来源于人工智能本身。微软小冰所生成的诗歌、作曲机器人所生成的交响乐均在此列。
尽管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物并不会对著作权制度产生真正的挑战,[3]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创造物所引发的著作权保护需求,注定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双重困境。
一、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及理论争议
无论在作者权体系,抑或在版权体系中,作者都是著作权保护的起点和中心。人工智能创造物“作者”角色的缺失,是其著作权保护法律问题的病根。对此,目前的解决思路是将人工智能解释为作者,或者将其他主体解释为作者,但在现有著作权法的基础理论框架下,这些解决思路所引发的理论争议都无法自洽。
1.背离了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基础
作者权体系的著作权法肇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作者权体系中,著作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专属于人类作者,是作者对于自己人格的延伸—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如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著作权仅指个人的智力创作。”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11-1条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仅仅基于其创作的事实,就该作品享有独占的及可对抗一切他人的无形财产权。”而人工智能创造物是由人工智能产生的,并不存在人类作者,其自然也就不属于作者人格的延伸。如果将人工智能解释为作者,那将是对作者权体系的根本性颠覆:为何毫无人格体现的人工智能也能产生类似于人类作品的创造物?作者权体系所理解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与感情”一说,是否只是立法者的一厢情愿?
将其他主体解释为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物是由人类设计、操作的人工智能产生的,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人类智慧,存在与人类之间的联系,[4]这种解决方案同样不可行:可以将人类看作人工智能的“元作者”,但不能将人类看作后续的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作者”[5]——无论是人类设计者还是操作者,在其头脑中事先并没有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构思,他们甚至无从预测、重复产生相应的人工智能创造物。如果将其解释为作者,相当于认为驯兽员是动物所作画作的作者,象棋发明人是各种棋局的作者,其本质是对“创作”的误解。
因此,给予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背离了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基础,面临着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
2.难以实现版权体系的立法目的
不同于作者权体系,基于功利主义说的版权体系不强调作者人格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因此并不排斥人工智能这一“非人类作者”。[6]基于此,版权体系早早地对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做出了规定,[7]然而这些规定同样经不起理论层面的推敲。
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充分阐述了版权体系的立法目的:通过给予有期限的著作权保护,激励作者继续创作与传播作品。然而人工智能创造物是由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无论是否给予其著作权保护,作为“作者”的人工智能都不会受影响;可能受影响的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类——设计者、操作者和拥有者等实际控制者,这显然偏离了版权体系的立法目的。有学者认为通过给予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可以促使其设计者和操作者更好地开发、使用人工智能,以产生和传播更多作品。[8]这一说法同样无法体现著作权法的激励目的:既无法证明激励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证明激励符合对价原则。[9]试分情况述之:情况一,如果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的操作者,既无法确定发挥激励作用—操作者并不能保证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数量和质量;[10]也不符合对价原则——操作者非创造性的付出,并不足以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激励。[11]情况二,如果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其初衷是希望设计者通过设计人工智能,生成更多、更好的人工智能创造物,但是这一激励目的已经由在先赋予设计者对人工智能的专利权、软件著作权实现,额外赋予其对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显然构成了重复、过度激励[12]——人工智能设计者以一次创作,换来了无限数量、无限时间的权利保障,显然也不符合对价原则。情况三,如果将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的拥有者,相较于前两种情况更是等而下之(有鉴于此说多援引法人作品的规定,下文将予以合并分析)。
因此,以激励为由给予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同样难以实现版权体系的立法目的。
3.超出“法人作品说”的适用范围
尽管存在上述瑕疵,仍不乏有学者依托功利主义说对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做出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人作品说”。此说主张沿用现有著作权法的法人作品规定,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问题[13]:通过将人工智能的拥有者视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作者,将著作权赋予拥有者,把人工智能创造物纳入著作权法的现有体系当中。抛开法人作品规定是否合理不谈,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也不能直接适用这一规定。
在传统的法人作品情况中,人类依然是实际上的作品创作者—立法者只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作品的权利归属于一个虚拟的法人主体而已。根据这一制度设计,人类作者仍然享有一定的利益,并能够以此与拟制作者对价:以电影作品为例,许多大制作电影的著作权均由制作公司享有;而电影作品的实际创作者,如导演、演员等虽然不享有著作权,但随着该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运作,这些创作者也能在经济报酬和个人声誉方面分享到收益。易言之,尽管作品的著作权归虚拟法人所有,著作权激励仍将作用于实际上的人类作者。然而如果对人工智能创造物适用法人作品规定,则只会催生单纯的垄断权,起不到丝毫激励作用。因为作为实际创作者的人工智能无法感知到精神激励,也无法分享经济利益,所有著作权收益都将归其拥有者所有。此时著作权法赋予人工智能拥有者的只不过是一种垄断权,一种对于“生金蛋的鸡所下的金蛋”的所有权意义上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显然并非著作权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严重违背了对价原则,不具有正当性。[14]
二、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实践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在自然权利说的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已无实践可能。而在功利主义说的理论框架下,按照后果论的路径展开分析,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陷入实践困境。
1.人工智能创造物不可识别性的实践困境
以规制后果进行衡量,无论在立法、司法实践中采用法人作品规定,还是其他权利规定(如邻接权),抑或著作权法框架以外的特别权利规定(如类似于外观设计的权利),都无法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造物在外观上是无法与人类作品相区分的——除非明确说明,否则无法判断一首诗、一支乐曲是否来源于人工智能。这种客观上的不可识别性决定了其著作权保护的实践困境,以下以博弈矩阵进行说明。
表1 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在现有著作权制度下的博弈策略
| 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 | |||
| 坦白 | 隐瞒 | ||
| 社会公众 | 付费 | C-P₁,M₁ | C-P₂,M₂ |
| 不付费 | C,0 | 0,0 | |
由于人工智能创造物在客观上的不可识别性,将其投入著作权市场时,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有两种策略选择:坦白或者隐瞒其来源。由此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将产生不同的博弈结果。
在现有的著作权制度环境中,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如果选择坦白,人工智能创造物将直接进入公有领域,无法得到著作权保护;如果选择隐瞒,则人工智能创造物将作为人类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坦白;付费)的策略组合显然是最理想的结果:双方各得其所,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能够获得M₁的收益,社会公众也能获得C-P₁的收益。但是这一策略组合注定无法实现,它劣于(坦白;不付费)和(隐瞒;付费)这两个组合,后两者才是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在人工智能控制者选择坦白的情况下,社会公众不付费的收益C显然要大于付费的收益C-P₁,因此博弈将以(坦白;不付费)告终。而在社会公众付费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隐瞒的收益M₂往往要大于坦白的收益M₁,因为隐瞒能够获得著作权收益,而坦白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获得收益,比如在人工智能创造物尚属稀有的情况下,发挥一定的广告效应,微软小冰的诗集发布便属此类。[15]除去个例,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将选择(隐瞒;付费)。考虑到长期博弈的因素,(隐瞒;付费)这一组合又要优于(坦白;不付费);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供给是不长久的。
简言之,在现有的著作权环境中,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将选择隐瞒人工智能创造物身份的策略,以换取社会公众的付费。这无疑将对围绕“作者”身份建立的社会评价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考虑到这一点,著作权法势必需要对人工智能创造物做出回应。
无奈的是,根据表2博弈矩阵的分析结果,无论是将人工智能创造物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还是给予其特殊保护,如著作权法框架内的邻接权,或著作权法框架外的其他权利,都不可能解决其著作权问题。
表2 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在制度变革后的博弈策略
| 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 | |||
| 坦白 | 隐瞒 | ||
| 社会公众 | 付费 | C-P₁,M₁ | C-P₂,M₂ |
| 不付费 | C变,0 | 0,0 | |
这是因为,上述做法都是通过降低社会公众在(坦白;不付费)策略组合中的收益C变,迫使其转投付费策略。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动摇博弈矩阵另一个纳什均衡(隐瞒;付费)的地位。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仍然可以选择坦白或者隐瞒,从而在(坦白;付费)和(隐瞒;付费)的策略组合之间自由切换。如果坦白的收益M₁低于隐瞒的收益M₂,即人工智能创造物特殊保护的力度,如保护期限、保护要求等,小于著作权保护的力度,则他们仍会选择隐瞒,制度变革的效用几乎为零。只有当人工智能创造物特殊保护的力度大于著作权保护的力度,即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坦白的收益高于隐瞒的收益,他们才会更倾向于坦白。但是反过来,人类作者也有可能借此浑水摸鱼,将自己的作品伪装为人工智能创造物。在此情况下,制度变革实质上提供了著作权法的替代方案:如果它是著作权法框架内的,那么就意味着著作权法进一步扩张;如果它是著作权法框架外的,那么就意味着著作权法被架空。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制度体系化的不合理:凭什么人工智能创造物能够获得大于人类作品的保护力度呢?因此,所有的特殊保护都是不可行的,摆在立法者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给予人工智能创造物与人类作品无异的著作权保护。但是这样做同样无助于解决人工智能控制者隐瞒的问题——表2的博弈矩阵仍将同时存在(坦白;付费)和(隐瞒;付费)这两种纳什均衡,立法者只是放弃了规制主动权,并不等于“无为而治”。至此,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保护实践彻底陷入了僵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博弈矩阵设计并没有考虑精神层面的利益,如将人工智能创造物伪装为人类作品而给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可能带来的名誉收益等。这是因为精神层面的利益很难量化,而且因人而异,无法作为一个普适性的考量因素。然而这一利益对于目前的博弈结果并没有质的影响,它只是加重了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选择隐瞒策略的砝码。
2.不可识别性的客观阻碍
如果从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不可识别性入手,采取增强可识别性的解决方案,似乎能够摆脱其著作权保护的实践困境。比如有学者主张记录下创作者的创作轨迹,以此证明他的作品并非复制或归属于人工智能[16];也有学者主张对人工智能的持有者实行登记制度[17]。结合上述方法,还可以采取惩罚隐瞒者的配套措施,以促使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选择坦白的策略。根据表2的博弈矩阵,这些都是不增加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坦白的收益,转而增加其隐瞒的成本的方法,同样可以实现(坦白;付费)的纳什均衡。可惜的是,这些方法的可行性都不算高。
其一,记录创作轨迹的做法并不符合创作规律,有许多作品是无法清楚说明创作轨迹的,以此为由不给予著作权保护并不合理。其二,全面登记人工智能的难度太高,即便在人工智能为数不多的今天,都无法保证登记所有的人工智能,并监控其产生及控制者的变动,遑论随着成本和技术门槛的降低,在人工智能数量可能实现爆炸性增长的未来实施这一方案了。其三,在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不可识别性的前提下,一切建构于制度层面的惩罚配套措施都只能是一纸空文;至于能否产生相应的识别技术,笔者也持谨慎的观望态度[18]。
三、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未来可能
行文至此,可得出如下结论:著作权法必须对人工智能创造物进行专门规制,否则人工智能的实际控制者会采取隐瞒策略,将其伪装为人类作品。但是无论立法者对人工智能创造物持何种态度—保护、不保护、部分保护,无论司法实践对人工智能创造物采取何种特殊规定—著作权法框架内的、著作权法框架外的,都无法妥善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不可识别性,而这种不可识别性又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因此,在功利主义说后果论的理论框架下,以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不可识别性为前提,探索人工智能创造物与人类作品的分流保护,便构成了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未来可能。
1.提高并设置不同的作品独创性标准
作为作品认定的一大实质要件,独创性标准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不同国家各不相同,两大体系之间存在差异。[19]在作者权体系国家,独创性标准体现了作者的“个性”,[20]意味着作者的人格与作品之间的联系;版权体系国家只是将独创性标准看作作品认定的一大“准入门槛”。因此,从功利主义说出发,强调独创性标准在现实操作层面的识别功能,将其作为著作权市场的“调节阀”,或有望部分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
第一,将原本抽象而主观的独创性标准具体化。尤其是在司法实务中,通过明确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强调“创”的因素,使只有达到较高独创性标准的创作才能构成“作品”,[21]提高准入门槛,从而限制著作权市场的总规模。
第二,针对不同的作品设置不同的独创性标准。对最有可能大量涌入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作品类型,如摄影作品、视听作品等,设置较高的独创性标准;对更有可能由人类作者完成的作品类型,如戏剧作品、曲艺作品等,设置较低的独创性标准。可以有针对性地降低人工智能创造物在著作权市场中的比重。
这一方案在最低限度改革著作权制度的情况下,有助于阻挡海量的人工智能创造物抢占著作权市场;在保证著作权市场秩序的同时,还可以发挥著作权制度激励高质量作品创作的作用。它并没有直接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不可识别性问题,而是通过提高标准的方式,帮助高质量的人类作品挤占人工智能创造物的生存空间。当然这一方案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首先便是可行性问题——如何将抽象主观的独创性标准合理地具体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别提根据不同的作品类型设置相应的独创性标准了。稍有不慎,就将导致由法律人来判断作品艺术成就的后果。在解决了可行性问题后,本方案还有可能面临立法伦理的拷问:当人工智能创造物构成了作品而人类作品却不被承认为作品时,[22]著作权法的立法意义何在?这是否意味着著作权法鼓励人类与人工智能展开竞争?
2.构建分层保护的著作权制度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扩张,今时今日的著作权人只需要完成创作这一动作,就能够享有蔚为可观的众多著作权权项——从人格权到财产权,保护范围无所不至。著作权制度的这一现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在此不展开论述,但正是著作权“获取的便利”与“保护的全面”之间的失衡,为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埋下了隐患。在信息稀缺的时代,给予作者便利而全面的著作权保护有助于激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但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继续沿袭甚至发扬这一保护模式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便利而全面的著作权保护能够保证作品的数量,却无法保证作品的质量和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过多过滥的作品权利还会产生类似“专利丛林”的困境。借解决此问题的机会,可以对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加以调整,构建分层保护的著作权制度:
第一,仿效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制度,设立在权项和保护期限等方面存在区别的两个层次的著作权权利——“注册著作权”和“自然著作权”。“注册著作权”须经登记方能获得,“自然著作权”仍沿袭传统的创作完成即取得的制度设计。两者具有不同的形式要求,享有不同的权利范围。
第二,“注册著作权”只能由人类作者取得。人类作者需要在登记时说明创作思路和创作过程,承诺自己为真实作者。如果在日后的维权过程中被发现登记作伪,如系人工智能创造物,则撤销该登记,并追究“注册著作权”人的法律责任。“自然著作权”仍采取“署名推定”原则认定作者身份。
第三,将精神激励与经济激励相分离,“注册著作权”人享有相应的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而“自然著作权”人只享有著作财产权。在进一步的细致设计过程中,还可以围绕“注册著作权”和“自然著作权”各自的具体权项和保护期限进行规划,但总体来说两者的区别不应过大。
通过给“注册著作权”设立门槛,并提供具有充分替代利益的“自然著作权”,可以区分博弈主体的收益偏好,引导其各取所需,以实现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创造物的分流。人类作者可能比较看重精神激励,并倾向于获得“注册著作权”;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控制者往往更看重经济利益,从而满足于手续简单的“自然著作权”。当然,仍可能有人类作品为求便利而满足于“自然著作权”的保护,也可能有人工智能创造物被精心包装后获得“注册著作权”保护——本方案无法保证绝对区分和隔离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创造物,只能在大概率上发挥分流作用。本方案的底线在于,即便有人类作者因无法描述创作思路和过程(如神来之笔等偶然性创作)而难以获得“注册著作权”,“自然著作权”也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保障。而如果人工智能创造物通过浑水摸鱼获得了“注册著作权”,其控制者就得承担丧失一切保护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因此在保障作者和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人类作品和人工智能创造物都能各得其所,在著作权市场上区分开来。本方案的上限在于,著作权制度的立法价值有可能通过这一设计得到发扬: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凝聚了作者智慧的创作——醉酒后的信手涂鸦和人工智能的演算一样,都不属于此类创作之列。只有愿意接受登记监督的作品才能获得“注册著作权”保护,其作者才能享有相应的精神激励。
本方案同样存在缺陷:如何证明创作思路等登记信息作伪仍然是一大难题,在现实操作中也许只能对人工智能实际控制者的大规模浑水摸鱼起到威慑作用;“注册著作权”和“自然著作权”的客体界限也很模糊,还需要对创作者做进一步的细致指导。而最大的障碍无疑来自《伯尔尼公约》,无论是对著作权登记的重启,还是对著作人格权的剥离,都违反了《伯尔尼公约》的规定。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上述方案在实际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上仍是利大于弊的。随着人工智能及其他“黑科技”的发展,著作权法所面临的难题还将与日俱增:建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著作权法能否跟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步伐仍是未知数,譬如在人机结合的未来,著作权法将何去何从?变局当前,抱残守缺实属不智之举,勇于变革才能让著作权法焕发新生机。
注释:
[1]ANDREW J W.From video games to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assigning copyright ownership to works generated by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computer programs[J].Aipla quarterly journal,1997,25(1):150-154.
[2]如李扬、熊琦的观点。冯飞.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专利保护并肩前行[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4-25(10).
[3]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148-155.
[4]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Z/OL].(2020-3-16)[2020-6-15].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30ba2cab36054d80a864ab8000a6618a.
[5]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98.
[6][8]ARTHUR R M.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Databases,and Computer-Generated Works:Is Anything New Since CONTU?[J].Harvard Law Review,1993(5):1050,1066-1067.
[7][17][22]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J].科技与法律,2016(3):488-508.
[9]著作权法给予作者的激励不是无条件的,其应当符合对价原则,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他人利益或者公众利益,从而导致制度结构失衡。徐瑄.知识产权对价论的理论框架——知识产权法为人类共同知识活动激励机制提供激励条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1):99-100.
[10]以微软小冰为例,重复地操作微软小冰只会产生大量文笔不通之作。著作权保护鼓励的是操作者从中“淘金”的韧性,但是这种“淘金”选择显然不能构成著作权保护的理由。AIPPI决议[R/OL].(2019-11-3)[2020-6-15].http://114.247.84.87/AIPPI/ztyj/jy/201911/t20191113_236228.html.
[11][12]MARK P,THOMAS M.From music tracks to Google maps:who owns computer-generated works?[J].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0(26):627.
[13]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3):3-8.
[14]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所有权与著作权的区别:一个人可以说用他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所有纸张都是他的财产,但是他不能说这些纸张上面的文档都是他的作品。通过法人作品规定给人工智能拥有者以著作权,正是混淆了这两种权利。
[15]全球首部!微软小冰推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N/OL].(2017-05-20)[2020-6-15].http://tech.sina.com.cn/roll/2017-05-20/doc-ifyfkkmc9892391.shtml.
[16]凯利.失控[M].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413.
[18]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本就是以人类为模仿和超越对象的过程,其创造物也只会越来越接近乃至于超越人类作品,很难想象设计者会主动追求、彰显其与人类作品的区别。
[19]吴汉东,曹新明,等.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2-43.
[20]姜颖.作品独创性判定标准的比较研究[J].知识产权,2004(3):8-15.
[21]事实上在司法实务中已经有类似的操作,如“应达到多少字以上才能构成文字作品”便是一种作品独创性标准的具体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