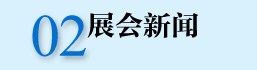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王迁、闻天吉: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摘 要】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后,我国通过新设信息网络传播权,配合使用既有的广播权、兜底权利的方式落实了WCT第8条的要求。这种立法模式切合法理,确保了法律适用的弹性,为网络版权的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我国还通过借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构建了网络环境下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近20年的网络版权法律实践过程,也是新问题不断产生、理论和实务经验不断丰富的过程。今后,我国应继续强化网络版权保护,但无论是直接规制网络用户行为,还是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义务,均不适用于我国。继续正确适用既有的网络版权立法成果,利用既有规则解决新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工作的核心。
【关键词】著作权法;网络版权;保护;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时,网络技术尚未普遍应用,网络版权保护未能成为立法工作的重点。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版权保护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2001年《著作权法》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等条款,[1]网络版权保护制度随之在我国确立。《著作权法》确立的网络版权保护制度在我国已实施将近20年,有必要对20年的网络版权保护历程予以总结,以期对今后的法律实践有所裨益。
一、网络版权法律制度的确立
1.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基本权利的确立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权”款[2]仅能控制以传统的有线、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和部分网络传播行为。为应对数字传播技术的挑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主持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以下简称WCT),这是我国确立网络版权法律制度的缘起。WCT是一部网络时代的版权国际条约,主要是为了提高成员国在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水准。WCT第8条规定[3]的“向公众传播权”弥补了《伯尔尼公约》的不足,将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的所有有线、无线传播作品的行为纳入了著作权的控制范围。WCT第8条的“向公众传播权”既包含控制交互式传播行为的“提供权”,又包含控制非交互式作品传播行为的其他“向公众传播权”。我国在2001年通过《著作权法》修订的方式引入了WCT第8条后半句规定的“提供权”,成为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通过比较中美落实WCT第8条的方案可知,中国方案在全面落实条约第8条规定的同时遵守了基本的法理,与美国方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能否使公众获得作品载体为区分标准,美国法院将WCT第8条控制的公开传播行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供公众下载且有人实际下载的行为,二是其他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前者由发行权控制,后者由表演权或展示权控制,同时这些行为又被认为构成复制行为。美国《版权法》规定发行是“以出售或其他转移所有权的方式,或者以出租、租赁或者借阅的方式向公众发行享有版权保护的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4]因此作品的发行必须涉及作品载体所有权或者占有的变动。[5]尽管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供公众下载以及实际下载的行为不涉及作品载体所有权的变动,但美国的多数法院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发行。[6]既然这种行为构成发行,就应该适用“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但美国从未承认网络环境下的权利用尽。[7]美国选择通过既有权利落实WCT第8条,虽然节省了立法成本,但违背了基本法理,陷入了发行行为无法适用权利用尽规则的逻辑怪圈。
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通过增设新权利的方式落实了WCT第8条。2001年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8]“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交互式传播行为,即WCT第8条中的“提供权”控制的行为。其他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转播无线广播作品的行为由《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控制。[9]当然,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不仅控制交互式传播行为和广播技术背景下的有线、无线传播行为,其他任何有线、无线传播行为均在其控制范围。例如网络直播尽管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控制的无线传播行为,仍然构成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依托《著作权法》第十条的弹性设计,《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就可以控制该类行为。[10]我国在落实WCT第8条的过程中恪守了基本法理,《著作权法》第十条的兜底条款确保《著作权法》可以应对任何有线、无线传播作品的行为,这表明我国在网络版权方面的立法技术已有相当进步。
2.网络环境下多方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
《著作权法》确立了版权人在网络时代的“向公众传播权”,但作品的网络传播涉及多方主体,由此产生的利益平衡问题无法通过“向公开传播权”解决。为此,我国在借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的基础上,于2006年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条例》保障了“向公开传播权”的实施,合理界定了版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权利义务,构建了网络环境下三方利益的平衡机制。
《条例》主要借鉴了DMCA的“避风港”规制和“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制度。《条例》为网络接入与信息传输通道服务、系统缓存服务、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信息定位服务提供了“避风港”,[11]允许这些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特定情况下不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条例》的“避风港”与DMCA的“避风港”不能等同。在DMCA出台之前,不少美国法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只要用户实施了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2] DMCA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进入“避风港”的资格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在适当情况下终止反复侵权者的账户”,还应“适应及不干涉版权人为识别或保护作品而采取的标准技术性措施”,[13]这就是所谓的“避风港”准入门槛。[14]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旦符合进入“避风港”的资格条件,法院就不能要求其承担严格责任,只能根据帮助侵权规则和替代侵权规则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因此,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帮助侵权责任、替代侵权责任的“归责条件”(不符合“避风港”的“免责条件”),则无法进入“避风港”,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或替代侵权责任;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符合帮助侵权责任、替代侵权责任的“归责条件”(符合“避风港”的“免责条件”),则可以进入“避风港”,无须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或替代侵权责任。可见,DMCA“避风港”的“免责条件”的反面就是帮助侵权责任、替代侵权责任的“归责条件”,但《条例》“避风港”的“免责条件”的反面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条件”。例如《条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15]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做明确标示,未必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避风港”的要求必然免责,但不符合“避风港”的要求未必承担法律责任,这导致《条例》部分“避风港”条款的适用受到了限制,这些条款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较之于“避风港”规则,《条例》的“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16]根据这一制度,权利人可以“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侵权内容,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删除其认为侵权的内容。同样,网络用户可以“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恢复被删除的内容。如果“通知”和“反通知”的信息矛盾,那么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使法院最终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也不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法律责任。但根据《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通知”制度和第十七条规定的“反通知”制度,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删除“通知”的内容,或者应当恢复被删除的内容。但作为《条例》借鉴对象的DMCA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17]这表明《条例》还未充分认识“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制度的意义。“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制度有利于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注意义务,有助于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内容采取必要措施。据此,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了注意义务,但未能对“通知”对象做正确判断,即使该“通知”对象确系侵权,也不能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删除“通知”对象而追究其法律责任。《条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删除“通知”对象,这表明《条例》对“通知-删除”制度的作用认识不清,因此在制度构建上存有瑕疵。
二、网络版权法制实践的发展
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之后,我国200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条例》,标志着我国的网络版权法律实践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网络版权法律实践的过程,也是新问题不断产生、理论和实务经验不断丰富的过程。
1.深入认识网络传播权利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入法的早期,局域网传播作品行为的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获得了较多的讨论。这表明,尽管我国的网络版权立法相对完善,但当时理论和实务界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还不够统一。例如就局域网传播作品行为的定性问题,争议的核心在于何为“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少观点认为,网络传播过程中公众获得作品的“时间和地点”不应受任何限制,否则该网络传播行为不构成交互式传播。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网吧通过局域网传播作品的行为曾被认定为放映行为或复制行为。[18]然而,许多信息网络传播都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不能让公众在任意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再如,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既然将作品复制到服务器是交互式传播作品的前提,那么复制权可以替代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2001年 《著作权法》修订之前,曾有法院认定将作品复制到服务器的行为构成对作品的复制,侵犯了作品的复制权。[19]以复制权替代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观点显然存在问题,这会导致权利人无法获得停止侵权的法律救济,更无法保障权利人获得充分的损害赔偿,因此至今已很少有人坚持这一观点。正因为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人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才能够不断深入,网络版权法制实践才能够蓬勃开展。
2.科学界定新型传播行为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不少新的传播现象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如破坏技术措施后对合法传播的作品设置深度链接的行为。不少学者认为,破坏技术措施设链的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20]另有学者认为上述设链行为的定性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将作品从原先不能为公众获得的状态转变成可为公众获得的状态才可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21]在破坏技术措施设链行为大规模出现之前,较为普遍的是对侵权作品设链的行为,较为权威的判决认为这种设链行为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22]但破坏技术措施设链的行为大规模出现后,设链行为的定性再度引发争议。实际上,无论何种设链行为,向公众提供的均是被链作品的网址,而非被链作品的内容。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设链行为未传播任何作品,显然不属于传播行为。经过大量讨论,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对设链行为作出了正确的定性,即设链行为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23]破坏技术措施后对合法传播的作品设置深度链接的行为,并未侵害版权人法定的权利,但侵害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属于破坏技术措施的违法行为。当然,司法实践是在正确运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理论的基础上才作出上述定性的,正确运用基础理论,也是网络版权法制实践不断进步的体现。
3.不断完善版权保护规则
网络版权保护的20年,也是版权保护规则不断完善的20年。早在2001年《著作权法》引入“向公众传播权”之前,我国就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布过网络版权保护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8号)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24]这一条款采用了“共同侵权责任”的提法,“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等措辞表明该司法解释区分了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行为。这一区分奠定了网络版权保护规则的根基,为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规则打下了基础。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方面,法释〔2000〕48号同样有较为科学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25]这一条款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过错责任,而非无过错责任。过错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注意义务的违反,因此法释〔2000〕48号第五条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行为的法律义务是注意义务而非审查义务,这为科学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奠定了法理基础。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具体规则,法释〔2000〕48号第五条也有明确的规定。该条款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仍不采取措施的应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用户侵权行为的情形。至于“明知”的具体判断方法,该条款规定“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即构成“明知”侵权行为,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通知-删除”规则。当然,较为遗憾的是法释〔2000〕48号并未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用户侵权行为的情形。
法释〔2000〕48号历经2004年和2006年两次修改未有实际变化。考虑到网络版权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入,既有的网络版权保护规则已经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于是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0号),该司法解释对网络版权保护规则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完善。
法释〔2012〕20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这一条款实际上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侵权行为仅承担注意义务,而非审查义务。法释〔2012〕20号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这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无论是“明知”还是“应知”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只要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即构成帮助侵权行为。法释〔2012〕20号还明确了所谓的“红旗标准”,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将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或者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感知的位置的”“对热播影视作品等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的”“其他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未经许可提供,仍未采取合理措施的”,均属于“应知”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
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侵权行为过错的认定问题,我国的司法实践也经历了从“红旗标准”到超越“红旗标准”的发展过程。根据“红旗标准”,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不可能不注意到用户上传的相对完整的热门影视、音乐作品,[26]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侵权行为具有过错。反之,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不属于相对完整的热门影视、音乐等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明显知晓侵权行为,“红旗标准”就不能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侵权行为也不承担责任。[27]然而,随着商业模式的发展,“红旗标准”在很多案件中无用武之地。为此,司法实践总结出了超越“红旗标准”的过错认定规则,[28]这一规则主要考察服务提供者采用特定商业模式的主观意图,重点关注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避免侵权。这一过错认定规则与美国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间接侵权责任的“引诱侵权”规则类似,是多年来网络版权司法实践经验总结的成果,[29]标志着我国网络版权司法保护的能力已日趋成熟。
三、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远景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版权保护水平持续提高,这是国内和国外两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国家版权局连续多年开展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有力打击了网络盗版行为,网络影视音乐产业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我国推动网络版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内因,是出于本国产业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的网络版权保护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不存在任何降低版权保护水平,甚至纵容网络盗版的可能性。
1.不建议加重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的责任
学界不乏提高保护网络版权保护水平的提议,如加强对用户盗版行为的规制,或者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加强对用户侵权行为的监控。前一种提议的典型是设立“三振出局”机制,尽管“三振出局”机制对网络用户的教育意义大于惩罚意义,[30]但考虑到成本问题,这一机制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一种提议显然是受到了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的影响,指令第17条“过滤器”条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版权内容的过滤义务,目的是为了协调欧盟著作权人与优兔(Youtube)等国外网站的利益冲突。但我国网络产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过高的法律义务并不利于网络视频、音乐产业的发展,这一提议同样缺乏可行性。
2.建议充分利用现有制度保护网络版权
考虑到网络用户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活动日益活跃,为实现网络用户、权利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我国在今后的网络版权保护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制度的作用,继续明确侵权行为和合理使用行为的界限。在过去,网络版权侵权行为以传播完整的影视、音乐作品为主,因为侵权行为较为明显,所以在权利人发出删除通知后,网络用户很少会通过反通知对抗权利人的通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用户创作、传播内容日益便捷,网络用户传播他人短小的作品如传播短视频或作品片段的行为,以及在他人作品基础上创作并传播新作品的行为日益多见。在权利人发出通知后,考虑我国合理使用认定的复杂性,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网络用户,均无法对作品传播行为的合法性作出专业、准确的判断。此时,权利人能否获得救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该删除被投诉内容,用户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三大问题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在侵权事实不明显的情况下,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不删除用户投诉内容,也不能绝对认定服务提供者违反了注意义务。只能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放弃享受“避风港”,而选择让法院适用侵权认定的一般规则。
法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必须重视网络用户发出的反通知。具体而言,在权利人发出侵权投诉通知后,如果网络用户在反通知中主张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且有表面上合理的理由,只要侵权事实并非过于明显,就不能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删除相关内容而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至此,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和权利人三方的纠纷,转化为用户和权利人之间的纠纷。而在用户和权利人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合理使用规则的细化至关重要。合理使用规则的细化,不但可以解决个案中用户和权利人的纠纷,其示范作用还可以规范网络用户的行为,进而实现网络用户、权利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结语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网络版权法律体系,有着丰富的版权保护经验,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尽管新型传播技术对现有制度有所冲击,且蓬勃发展的网络产业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有法律制度仍然能够满足实践的需求。如果冷静分析网络版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大部分问题均可以通过现有制度解决,目前谈对现有制度的根本性革新还为时过早。继续细化完善现有网络版权保护规则,利用现有规则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工作的核心。
注释:
[1]2001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
[2]M.Ficsor,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494-495.《伯尔尼公约》的第11条第1款第2项、第11条之二第1款第1项和第2项、第11条之三第1款第2项、第14条第1款第2项和第14条之二第1款是《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权条款。
[3]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条款规定:“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11条第1款第2项、第11条之二第1款第1项和第2项、第11条之三第1款第2项、第14条第1款第2项和第14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
[4]17 U.S.C.A.106 (3)
[5]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lnfonn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ghts),Washington,D.C.(1995):70
[6]例如著名的Napster案审理法院认为,P2P软件用户未经许可将MP3音乐文件置于“共享区”供其他用户下载的行为构成“发行”,A & M Records Inc v.Napster Inc,239 F.3d 1004 [2001]:1014.类似案例见 Warner Bros.Records,Inc.v.Payne,2006 U.S.Dist.LEXIS 65765 [2006]:3-4
[7]Digital Choice and Freedom Act of 2002 (H.R.5522) introduced in Oct.2002,Section 4;Benefit Authors or withoutLimitingAdvancement or Net Consumer Exceptions (BANLANCE) Act of 2003,108th Congress,1st Session,HR 1066(March 4,2003)
[8]《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12项
[9]《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11项
[10]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可以视为使用“兜底权利”的实际案例。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初字第10396号民事判决书
[1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条
[12]相关案如“花花公子”案,参见Playboy Enterprises v.George Frena,839 F.Su:1552
[13]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
[14]17 USC 512 (i) (1).参见陈绍玲.避风港准入门槛在我国的不适应性分析[J].知识产权,2014(12)
[1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
[16]《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条
[17]17 USC 512 (c),(d)
[18]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朝民初字第07065号(认定网吧侵犯“复制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东民初字第1503号(认定网吧侵犯“复制权”和“放映权”)
[19]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二中知初字第18号
[20]陈加胜.信息网络传播权与链接的关系[J].电子知识产权,2012(2)
[21]王迁.论提供“深层链接”行为的法律定性及其规制[J].法学,2016(10)
[2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高民终字第1184号
[2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73民终143号,另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4741号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8号)第四条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8号)第五条
[2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二中民终字第19082号
[27]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89号
[28]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高民终字第2581号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0号)第十条
[30]陈绍玲.“三振出局”版权保护机制设计研究[J].中国版权,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