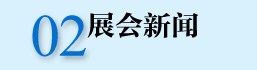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李自柱:中国政法大学
【摘 要】专有出版权的本质是著作权人通过合同将其复制、发行权授予出版者而产生的出版者专有复制、发行作品的权利。在对专有出版权具体内容未约定的情况下,其效力范围应该是授权作品的整体内容或者与授权作品整体内容基本相同、实质性相同的内容。
【关键词】专有出版权;权利性质;效力范围;汇编作品
1 案情简介
苏霍姆林斯基的继承人奥莉加与A出版社签订合同,授权A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复制发行《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并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其无权再授权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作品。A出版社据此出版发行了该书,其中第一卷包括《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问题》《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集体的方法》;第二卷包括《年轻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给教师的100条建议》;第三卷包括《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公民的诞生》《给儿子的信》;第四卷包括《帕夫雷什中学》《和青年校长的谈话》;第五卷是论文集,包括68篇论文。其中,第二卷字数542千字。在上述合同期内,奥莉加授权B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专有出版发行作品《给教师的建议》。随后,B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字数219千字。该书与上述《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第二卷中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内容基本相同。
A出版社认为,B出版社侵害了其对《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享有的专有出版权。一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二审法院认为,专有出版权不是邻接权,而是复制权、发行权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其指向的客体范围是图书的整体或实质性部分,不能延及图书中各个非实质性的组成部分。B出版社仅使用了《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的部分内容,且A出版社并未举证证明或说明《给教师的100条建议》是《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的实质性部分,故B出版社未侵害A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①
2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专有出版权权利性质及其效力范围问题,下面分而论之。
2.1 专有出版权的权利性质
专有出版权被规定在《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一节“图书、报刊的出版”中,而第四章规定的不是著作权,而是“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即邻接权。从该体系上,专有出版权很容易被认为是出版者权,是一种邻接权[1],但该认识有误。对该权利的性质,不能从该法律体系上理解,而应当从文意解释、历史解释等角度探究。
《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从该条文意讲,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来源于出版者与著作权人的合同约定。出版者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根据在于合同是否有约定。如果著作权人通过合同授予了出版者专有出版权,则该专有出版权即受法律保护,如果未授予,则出版者不享有该权利,受法律保护无从谈起。可见,专有出版权是通过合同创设的权利,而非出版者的法定邻接权。
1991年的《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合同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合同期满可以续订。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根据该规定,出版者和作者在合同中能够约定的仅是不超过10年的合同期,只要双方签订了合同,那么出版者根据该规定即享有了合同约定期间内的专有出版权。可见,在该法中,专有出版权是出版者的法定权利。但在2001年修法时,该条做了较大修改,出版者的该项法定权利改为了上述通过合同约定产生的权利。从修法的历史过程可知,将专有出版权规定为一项通过合同产生的权利是立法者的有意选择,这“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侧重于对作者权利的保护”。[2]
虽然专有出版权是通过合同产生的权利而非法定邻接权,但该权利却又不是一种任由当事人创设的纯粹的合同债权,而是著作权人将其对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通过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在出版行业常表现为出版合同)许可给出版者行使的结果,即其权利来源是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其权利的内容、期限、行使等不能完全由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意思决定,而要受到复制权、发行权的权利行使规则等的制约。因此,专有出版权的本质应该是著作权人通过合同将其复制权、发行权授予出版者而产生的出版者专有复制、发行作品的权利。合同是该权利的创设手段,著作权人的著作权是权利来源。本案中,二审判决对专有出版权的权利性质的认定符合上述文意解释和历史解释,值得肯定。
另需说明,有观点认为只有具有合法复制和发行资质的出版社才有资格享有专有出版权。[3]本文认为,该权利虽名为专有出版权,且事实上也均是由出版社实际行使,但其并非专属于出版社享有的权利。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行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享有某一权利并不必然能够行使该权利。如,作者可以享有某些违法作品的著作权,但却因作品传播方面的管制,其不一定能够行使著作权。专有出版权的本质是作品的专有复制、发行权,任何主体均得享有。虽然享有该权利者因不具备出版发行资格而不能实际行使该权利,但不能据此认为该权利只能由出版社享有。
2.2 专有出版权的效力范围
专有出版权的效力范围包括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内容范围等,即出版者被授予的专有出版权在何期限、地域范围内以及作品何种内容范围内有效,其关系到著作权人和出版者权利范围的划分以及专有出版权的保护问题。
关于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较少发生歧义,本文不作讨论。疑惑较多的是作品内容方面的效力范围,即授予出版者专有出版权后,出版者在作品内容何种范围内享有专有权利?他人出版的作品与授权作品有多大比例的相同或实质性近似才属于侵犯专有出版权?他人抄袭作品后,是著作权人还是出版者有权利起诉?
根据专有出版权的权利性质,其是通过合同约定产生的来源于著作权的权利,因此,其权利内容首先应该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如果合同约定不清楚,则需要根据合同解释规则予以合同解释,且受复制权、发行权权利本身特点等的限制。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根据该规定,在合同对专有出版权具体内容未约定的情况下,出版者享有的权利范围为“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原版”即授权作品的全部内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修订版”一般是对“原版”修改增删形成的新版本,且通常情况下修改增删的仅是“原版”的局部内容,两者仍是同一作品,其内容不会相差甚大足以使人认为“修订版”实质上已经成为不同于“原版”的新作品。从对“原版、修订版”的该理解可以得出,在对专有出版权具体内容未约定的情况下,其权利范围应该是授权作品的整体内容或者与授权作品整体内容基本相同、实质性相同的内容。本案中,二审判决对A出版社从权利人处取得的对《苏霍姆林斯基五卷本》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的权利范围的解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上述解释不仅划清了专有出版权的保护范围,而且也界分了著作权人与出版者之间的权利界限。前者表现为“第三人不仅不得出版相同的作品,还不得出版实质上相似的作品”。[4]后者表现为“作者在授予某一出版者以专有出版权以后,不得将自己的同一作品或实质性相似的作品许可给第三人出版”。[4]同时,只有在第三人出版同一作品或实质性相似的作品时,才侵犯专有出版权,出版者才有资格主张权利,但此时著作权人则无权主张权利。而在他人抄袭作品局部,该局部不构成作品的实质性部分时,侵犯的则是作者的著作权,而非专有出版权,此时只能由作者主张权利,出版者则无权主张。有人可能会认为此处存在一个悖论,即他人抄袭作品部分时作者有权利起诉,但抄袭作品全部时,作者反而无权起诉了。其实,这正是著作权人和出版者之间的权利划分界限。著作权人授予出版者专有出版权后,出版者而非著作人即独占地享有了作品整体所占有的市场利益,但作品整体所占有的市场利益与作品局部所形成的市场利益不是重叠的,少部分抄袭作品的内容一般不会对该整体作品的市场占有率造成影响,但该抄袭行为确是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两者的利益分割是比较清楚的,在抄袭作品整体时,受损的并不是作者而是出版者的市场利益,因此上述悖论并不成立。因此,从深层次看,著作权人和出版者之间权利界限的划分根源在于市场利益的分割。所以,在判断第三人出版的作品是否与授权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作品或者是否属于授权作品实质性部分时,该作品是否能够起到对授权作品的市场替代效果就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而相同字数的多寡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
汇编作品“是一种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的作品、数据或其他信息的集合”[5],“受保护的汇编作品必须是经选择或者编排的内容的集合,其受保护的是结合了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②所以,尽管被汇编的作品是汇编作品的组成部分,但二者是不同的作品,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与被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均是独立的权利,两者均是可以被单独授权的对象,具有不同的市场利益。著作权人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自己创作的作品并加以编排形成汇编作品后,其有权将该汇编作品及被汇编的作品各自单独对外授权。获得汇编作品专有出版权的出版者不必然得到其中被汇编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也不必然能够排除他人出版被汇编作品的行为。如果被汇编作品不是汇编作品的实质性部分,他人出版该被汇编作品不会给汇编作品的市场利益造成损害,则汇编作品专有出版权人无权起诉被汇编作品的出版者。本案中,A出版社获得专有出版权的作品正是汇编作品,而B出版社获得授权并出版发行的是该汇编作品中的一部作品,该作品未构成汇编作品的实质性部分,两作品具有不同的市场利益,基于上述理由,B出版社的行为不构成对A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
3 结语
著作权是由复制权、发行权等众多权利集合在一起的权利束,这些权利通过流转与著作权人相分离,形成了著作权人与众多被授权人相关权利相互分割的复杂状态。只有通过对一项权利的效力范围的准确界定,才能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边界和利益分配。专有出版权正是著作权人和出版者通过合同分割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的结果,而只有在弄清其权利性质的基础上,对其效力范围进行准确划分,才能区分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权利范围。本案对此做出了有益探索,本文试图对此做出法理注解。
注释
①详见(2015)朝民(知)初字第39059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1080号民事判决书。
②(2015)京知民终字第1195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1]谭小军.我国专有出版权几个问题的探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2]姚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3]李扬.专有出版权的性质和控制范围[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39(3):2-5.
[4]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王迁.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