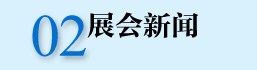2014年5月底,全球研究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全球资助学术出版的大金主云集于此,讨论全球学术出版界的问题。这类会议,自然少不了顶级学术期刊的参与。《自然》总编(editor-in-chief)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出席了此会,果壳网藉此机会采访了他。
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学术期刊之一,创刊于1869年的《自然》(Nature)杂志涵盖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和应用科学等领域,也是而今所剩无几的涵盖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一。2012年,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在上海设立独资公司,作为麦克米伦集团的一部分,自然出版集团旗下《自然通讯》派驻了编辑,他们属于全球编辑团队的成员,在执行主编印格致的带领下,旨在增强与中国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的沟通联络。

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图片来源:《自然》集团
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博士是《自然》创刊以来第七任总编。他的学术背景是大气物理,曾获英国莱斯特大学博士学位。他在1979年加入《自然》成为初级编辑,彼时《自然》上完全没有纯物理的内容,在他的参与努力下,《自然》逐渐成长为物理学重镇。即便如此,他觉得“我对物理学越来越着迷,《自然》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我了”,更重要的是,英国国家物理学会创办了一本新刊《物理世界》,在申请后他获任主编。1995年,在前任《自然》总编约翰•马多克斯退休后,他担任新一任《自然》总编至今。
坎贝尔说,他从小就对飞行器感兴趣:“我会开飞机,年轻的时候有飞行员执照。”他在学校期间还造过火箭发动机,不过最后还是“伴随一声巨大的‘bang’炸掉了。”他还对天文学感兴趣,喜欢科幻小说,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始终扎根于科学”。现在,他一大爱好是音乐,空闲时会自己弹弹钢琴,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是德彪西和贝多芬。
作为一位期刊总编和科学家,坎贝尔博士与果壳网科学人畅谈了《自然》杂志、开放出版业、学术规范及学术界现况等话题。
《自然》为研究者服务
科学人:身为《自然》总编,你每天都要做哪些事情?
菲利普•坎贝尔:我要和编辑人员交流探讨目前及今后的出版内容,他们既包括《自然》及其系列期刊的编辑们,也包括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的员工,因为现在自然出版集团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已整合在一起,我们一家公司同时提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我也为《自然》写很少量的社论,并为公司发展提供建议。
我和我的编辑们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拜访实验室,和研究者沟通。拜访实验室的经历让我学到一件事:会见实验室领头人和博士后甚至研究生也是同等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时候对于出版过程了解很少,我们可以帮忙澄清一些误解,鼓励他们勇于发表自己的研究。
科学人:有人认为《自然》是“学术期刊中的通俗杂志”,你们对它是如何定位的?
菲利普•坎贝尔:1869年《自然》期刊创办的时候,的确是面向所有人的,即非专业人员、普通公众,还有科学家。大概五年前,我们进行了一次改版重新发布,推出在线版本,我们决定把《自然》作为面向研究者的刊物,而不再面向大众。不过,这里所说的研究者指的是研究者整个群体,比如说,很多生物方面的论文,是写得能让物理学家也看得懂。所以和专业论文相比,还是比较好懂的。此外,《自然》当中还有关于科学本身、公共政策、社会和伦理等议题的内容,所有人都能看懂。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无论是公众还是科学界内部人士,都可以读这些文章。
科学人:所以事实上《自然》里既包括大众可以阅读的部分,也包括面向科学家的部分?你们如何平衡这两者?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不做平衡。我们只是每天、每周选取我们最感兴趣的内容。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科学研究者,他们要比普通读者更想要看到更多的数据、更详尽的信息,所以我们会更多地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只是发表我们能找到的最好论文”
科学人:《自然》、《科学》和《细胞》被很多人认为是科学界最好的三本期刊,《自然》是否和其他两家存在稿源竞争关系?你们是怎么处理这样的竞争的?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好编辑工作,让研究者愿意由我们来编辑处理他们的论文。
我们的编辑经常去拜访研究者,和他们沟通,了解他们在做的具体科研项目。我们希望发表最有意义的研究,所以我们希望研究者能认可我们对论文的良好判断力,我们会找优秀的审稿人,会给论文提供好的建议,并以合适的方式发表这些论文。这就是我们所有能做的。我们不会通过负面评论其他期刊的方式参与竞争。
科学人:有不少期刊依靠提高影响因子来竞争,手段之一就是发表综述文章。《自然》对于综述性文章有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又用什么手段提升影响因子?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乐于发表指明重要趋势的综述文章,一年中随时都可以发表。有些期刊考虑到影响因子的计算方式,喜欢把所有的综述文章放在年初时发表。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有一篇发一篇。我们不会策略性地多发综述文章。至于影响因子,其实它是被少数引用量巨大的论文主宰的。《自然》会发表很多文章,大部分的引用量也很低,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些论文,因为我们选择发表文章的时候不会考虑引用量——事实上引用量也很难事先预测。我们所做的就是发表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论文。我们从不设编辑委员会,我们有同行评议人帮助我们,我们的编辑一直是选定文章和做最终决定的人,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拜访实验室、阅读论文,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自然集团的所有期刊都这样,因此我们比较特别。
你问我怎么提升影响因子?我们只是发表我们能找到的最好论文而已,年复一年,一直如此。而从结果来看,人们似乎认为我们做得还不错。
科学人:那么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文章?
菲利普•坎贝尔:可以是技术上的突破,能够造福很多研究者的那种。也可以是澄清了一个许多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还可以是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文章。偶尔我们也会发表那些科学上或许没那么重要,但是和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论文,比如一种疾病的流行病学——也许在流行病学上没什么太新的东西,但是这种疾病目前非常引人注目,需要得到结果。但这只是少数情况,我们主要还是发表科学方面的文章。我最喜欢的论文,都是有关最新的发现,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第一次发现环绕其他天体的行星,还有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种史前小型人属佛罗勒斯人,论文都发表在《自然》上。这些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有关论文也是我最喜欢的。

2004年10月28日的《自然》封面文章报告了佛罗勒斯人的发现,这是本世纪古人类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图片来源:《自然》集团
开放获取期刊并不一定导致质量下降
科学人:目前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是学术出版行业的热点,自然出版集团对此有没有跟进?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有许多开放获取的期刊。自然集团旗下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论文中一部分是开放获取的,该刊创立至今发表了大约1000篇开放获取文章。《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的论文全部是开放获取的,目前总共发表了约9000篇。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说所的开放获取,是指“金色”开放获取,也就是作者付费、论文发表后立刻成为开放状态。另一种模式称为“绿色”开放获取,即作者可以在六个月的保留期过后把论文上传供所有人免费获得,我们全部的期刊都满足这一模式。
除了这些,我们还开始发布一系列“Nature Partner Journals(NPJ)”合作期刊。比如我们刚刚推出的《NPJ生物膜和微生物群》,这也是金色开放获取的期刊。再比如,本月我们还会发行一种新的开放获取期刊,名为《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它发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论文,而是对数据的描述。
科学人:而今开放获取期刊每年都发表数量极其巨大的文章,你认为这种模式是否会导致文章质量下降?
菲利普•坎贝尔:这不一定。开放获取的商业模式是作者支付费用来负担选稿流程,只要支付费用的人愿意为这个遴选过程付钱,文章质量就不会下降。我个人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开放获取和订阅形式会混合存在,这样就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了。诚然,标准太高、发文太挑剔的期刊成为开放获取期刊有困难;但我们既需要高门槛的杂志,也需要不那么精挑细选的杂志。而且对于要求严格的杂志,研究者也愿意付更多的钱。我不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创者们会牺牲质量,自然出版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开放获取出版商,我们当然也不会牺牲质量。
开放期刊这种模式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问题:如果你推出一份开放期刊,立刻就开始赚钱,就能收回发行成本;而传统模式下要依靠订阅,创办期刊就是一笔投资,要好多年才能收回投资。然而,如你所言,由于开放获取这个商业模式来钱很快,有些糟糕的出版商就进入了市场,无视标准地发表毫无价值的文章。我认为唯一去芜存菁的办法,就是看看他们以前都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及其标准。比较好的是,那些糟糕的期刊很快就会被发现。
同行评审是个成功的制度
科学人:研究者常常抱怨说一篇论文要评审很久才能发表,他们自己也觉得评审别人的文章是巨大的负担。你觉得现行同行评审制度让人满意吗?有没有什么改进意见?
菲利普•坎贝尔:人们常说同行评审是最不糟糕的办法,对此我依然赞同。我还没有见到别的能解决问题的系统。有些期刊在尝试“开放同行评审”,前景如何还有待观察。在自然出版集团内部,如果一份期刊在同行评审后决定不发表某篇论文,我们会推荐论文作者选择集团内的另一份期刊,评审者的意见也会一并转交,从而缩短发表研究的时间。我们也总是催促评审者尽快回复。我觉得自然集团的期刊都很幸运,毕竟评审者还是喜欢为我们审稿的。作者其实也可以从同行评审过程中获益。当发表小鼠全基因组测序的时候,我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著名基因组研究者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站起来说,《自然》反馈给他们许许多多难对付的评审意见,但他们对此十分感激。我们追求质量,研究者也因此尊重我们。
科学人:你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术不轨行为是什么?同行评审没能及时揭穿它,是这个体系的缺陷吗?
菲利普•坎贝尔:我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是物理学家詹•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ck Schön)。他发表了……我都不记得多少篇了,但是光《自然》就撤了他7篇稿子,《科学》和《物理学评论》也撤了差不多同样数目的论文。这表明合作论文时真的应该非常谨慎。舍恩当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这是一家很受尊重很受信任的研究机构,两位论文合作者在业内也很有名望,但是他们身在德国,而舍恩在贝尔实验室准备材料和数据。舍恩的合作者相信他的材料和数据,但是论文发表不久之后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完全不同领域里的论文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数据(因为领域不同,审稿人也不同)。很快人们发现这完全是胡扯,我们迅速撤掉了所有论文,贝尔实验室也立刻建立了外部调查组,组长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材料学教授。后来我去见他的时候问过他,“像舍恩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这太明显了,论文一发出来,研究者们立刻就能发现啊。他的回答是:每个领域里你都有不可理喻的人。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人。完全不合逻辑。我想他是对的,我也想不出别的解释。
不过要知道,编辑和审稿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论文是造假了的,因为你看不到实验是怎么做的,你只能信任他的数据。所以,我们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不是最终的定论。任何宣称都要靠整个科学界群体的验证——有时候是专门去重复原始实验,有时候是以其为基础继续推进研究看看能否行得通。只有那时你才能确认一篇论文是不是正确的。这一次系统很快就发现了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系统是成功的。
预印本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科学人:近一两年中的几项大的科技新闻,比如希格斯玻色子、原初引力波和仙女座星系疑似伽马暴,都是未经同行评审就以新闻发布会、预印本或者社交媒体的形式流传开来了。你觉得这会影响研究者交流的方式吗?对媒体的科学报道的影响又如何?
菲利普•坎贝尔:类似的预印本模式在物理学界已经使用了很多很多年,甚至早在网上文库出现之前就有了,所以我觉得研究者群体里这不算全新的东西。他们知道这是未经验证的内容,所以会更谨慎地看待它。但是对于新闻行业而言,他们看预印本就会有危险——比如来自某个著名科学家的论文,他们会觉得是可信的,但大牛也会犯错。又或者一篇推测性的文章,不能算错,但是在外人看来也许就像是言之凿凿地下结论。所以任何想报道预印本的记者,都应该做同行评审——比如给业内专家打个电话。
科学人:你认为科学家有必要把他们的东西告诉大众吗?
菲利普•坎贝尔:先说公众这边吧。我认为任何科学家只要有为大众写作的天赋,那就有为他们写作的职责。毕竟,研究经费还是来自公众对吧?你在花纳税人的钱,他们有权知道你为什么花这笔钱。当然,有时由职业记者来写最好,但还有些时候,科学家本人的声音能带来更多的可信度,尤其是公众辩论的话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科学家写博客是个好主意。当然这也有风险,有的科学家写博客可能会不负责任,但人们应当学会如何判断。我认为,为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为了让科学家的信息能传达给大众、而不是被人曲解,科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而且,年轻人如果对科学有兴趣,他们看到科学家的文章,他们可能会得到激励。
科学人:比如布莱恩•考克斯?据说他吸引了很多女生学习物理。
菲利普•坎贝尔:是啊,我们很多人都嫉妒他的天赋。
科学人:是嫉妒天赋还是嫉妒脸?(笑)
菲利普•坎贝尔: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寻常的天赋。(笑)
中国学术界的进步令人惊讶
科学人:自然驻上海办公室开张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来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有何进一步计划?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上海办公室的编辑是全球编辑网络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并不只处理来自中国的论文。我们的编辑一直在和学术界沟通,我们开设了训练课程,帮助研究者学习如何在期刊和公众那里展示他们的成果;我们还提供编辑服务,提高论文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些服务和我们的期刊投稿是相互独立的,换而言之,如果你先让我们帮忙编辑论文再提交给我们的期刊,这对我们的审核过程没有什么影响。

《自然》驻上海办公室墙上的海报。图片来源:《自然》集团
在出版方面,我们还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合作出版一些刊物,比如去年我们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推出了英文期刊《园艺研究》,今年五月我们和中科院电子所合作出版开放期刊《微系统与纳米工程》,这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九个合作期刊。我们还与大学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比如去年我们和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发布鸭全基因组论文,上个月我们和浙大联合发布H7N9禽流感生物标记物的论文。
在编辑方面,我们会继续拜访研究者,继续关注那些有意义的发展领域。这样,我们到其他国家时就会对别人说:“嘿,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在做哪些研究?”。
科学人:中国研究者常常对于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这样的量化指标过度热心。你觉得这是个严重问题吗?
菲利普•坎贝尔:作为证据的一部分,你需要去看数字。但是解读这些数字要非常谨慎。此外,在观察一些机制的运行时,也可以使用数字,比如整个国家或者所有期刊的情况,这时你可以用影响因子。但是以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衡量单个研究者,这就有点危险了。另外,有些领域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衡量的,比如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他们发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会出版专著,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是在政府报告里,不是以简单的办法就可衡量的。数字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需要更精细的办法来量化和衡量研究者的影响力。
科学人:你觉得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菲利普•坎贝尔:对啊,你们觉得为什么呢?(笑)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很悠久,描述这些科技成就的汉语也很古老,但以英文阐述中国科学研究的历史还相对较短,所以中国没有一本使用英文的国际知名期刊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中国对科学事业的持续专注令人惊讶,假以时日,有理由相信中国会诞生一份国际知名的英语期刊。到时候我们会努力和他们竞争的。
科学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年轻学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菲利普•坎贝尔:简单地说,就是:“敢创新,多小心”。
一方面,要有创造力,富有想象力,批判性地思考科学想法和概念,并且尝试找到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有趣的挑战。在你的研究生涯里,应当永远专注于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你在求知上没有雄心,不敢运用你的想象力,那么你永远只能当一个追随者。
另外,不要试图走捷径。这不仅仅是说给中国学生的,而是说给所有人的。而今,各国的青年研究者都有发表文章的压力——特别是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大胆断言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如果在发表前不非常非常仔细地检验这些断言,那就是坏事了。在我自己还是个研究者的时候,每当我对我老板说我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新东西,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不信”。但他是对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得回去检查为什么你的仪器会给你发出这个看起来有意义的信号。最后,你多半会发现,这是自然的力量、设备、测量仪器和你之间一些小的共谋。我很严肃地说,在科学领域,任何在提出主张前不进行极为严格的自我评判的风气,都有导致科学失去公众信任的风险。
因此,发表科研论文时要谨慎小心,要花时间好好做研究,因为如果弄错了,如果急于求成下结论,或试图走捷径,那没人会原谅你的,你的名声会永远受损。(编辑:C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