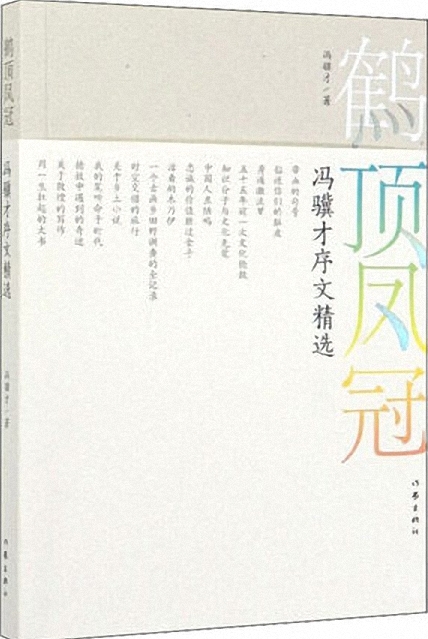
“作品史也是作家的生命史。”文学是冯骥才的至爱,“我的第一表达方式是文字。我相信,只有文字才是最深刻的,只有文字可以精确地刻画思想,只有自己的文字才是自己生命的文献。”他以切身体会谈文学,谈散文和小说,认为散文和小说在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实”二字上殊途同归。小说重文本,表明作家的本领;散文重人本,直接显示作家的气质,是一种“自我的文学”,作家看重散文,乃是一种“自我的珍惜”。然而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作品要献给同时代人,作用于社会,也要留给后人”。
冯骥才的作品切中时代的脉搏,倾听历史和未来的声音,在别人忽视之处,凝聚自己的目光。在他看来,历史是活着的,不仅存在于文献、史书、博物馆和日渐模糊的岁月里,也存在于人们的观念、话语、行为、习惯和下意识中,然而“不管什么样的历史,都需要正面和诚实地去面对,本质地去追求,科学地去认识”。
“我天性喜画,画在文先。”绘画这一爱好来自冯骥才对美的天然追逐与共鸣。他以作家的初心、画家的情怀,一边写作,一边画画,写作累了,用画笔调剂,涂抹尽兴,回到书桌,两支笔交替使用,无一废弃。在画中,他也面对现实思索,带着问题探寻,站在文化的高度审视。
自本世纪初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他就已然从书斋走向了田野,以实际行动完成大地上的书写,为濒危的文化遗产身体力行,奔走呼号,并以历史和前瞻的文化眼光,借由现场的深入调研、科学规划将这件事做到筋疲力尽,做到极致。20年来,他打捞《亚鲁王》、进宝斋伊德元剪纸、中国木版年画,作《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和城市、地域的文化遗存盘点,竭力将民间文化这种“生活的、人的、自发的文化”存录下来,建立永久性档案,保存个性化的民族文化基因。回顾多年的辛苦奔波,他自比堂吉诃德,但也并无悔意,只因他对自己做的事深怀感情:“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它不是美丽和无机的学术对象,而是跳动着脉搏和危在旦夕的文化生命。”为了挽救这生命,他历经了沧桑,也饱含着骄傲。
“记录历史和传承文明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至于他的第四驾马车——教育,则与他的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相融互通。四驾马车,并驾齐驱,砥砺前行,朝向一个善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