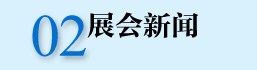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涂凌波、王子薇: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线下知识场所暂时性“关闭”,社会生活空间的“隔离”引发了传播中的具身性讨论与线上知识流动的新问题。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方法,考察了四种知识的线上传播状况。研究发现,具身性对于学院知识等专业知识的传播依然十分重要;知识“围墙”的消解促进了各类线上知识的流动,但网络中依旧会形成新的权威性知识节点,知识需要被确证;媒介的偏向决定了知识流动时的媒介载体,知识的重要程度影响其流动是否均匀;系统化的知识习得仍是抵抗信息超载与知识危机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隔离;具身性;知识传播
2020年初,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蔓延,我国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以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人们在空间上相互隔离,减少社会流动和具身性传播,进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传播场景。在以往的日常生活节奏中,线上信息传播、知识消费的特点被普遍认为是移动、碎片化和娱乐化的。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们的身体处于比较固定的空间内,居家生活、学习、办公使我们的个体时间安排变得相对齐整,更多类型的信息和知识出现在云端。尽管空间隔离所带来的知识流动变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只是暂时的、非常态的,但是这一新现象促使我们思考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是否可以离开特定的场所,以及线上知识传播与身体、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
本研究运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主要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通过定义研究问题、识别和选择社区、社区参与式观察、资料分析和解释、撰写研究发现等五个步骤,获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1]在2020年1月末至3月中旬这段时间,研究者参与观察了5场以上的网课教学,多场书店和剧院的“云端分享会”“云端放映会”,并做了网络民族志记录。同时,通过在线深度访谈获取网络民族志资料,对普通网民、网课教师、网课学生、知识付费用户展开半结构式访谈(20个问题),获得访谈录音资料为58365字。
本研究旨在考察空间隔离的社会背景下线上知识是如何流动的,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第一,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线下场所临时“关闭”后,不同类型的知识是如何在线上流动的?第二,个体的社会时间从碎片化重归齐整后,人们获取到的知识是否依旧是碎片化的?第三,线上知识传播之于人们的意义何在?
一、从传统知识到线上知识:知识的分类与传播特征
“知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史传统。关于“知识”的定义十分宽泛,比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D.布鲁尔(David Bloor)就认为“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2]。与科学、哲学知识不同,知识社会学主要讨论建立于共享的感觉与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如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指出,其研究主题更关注常识性知识,这一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3]20世纪以来,社会学家习惯将知识分类然后展开研究。罗伯特·帕克(R.E.Park)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讨论基础上,将知识分为熟识性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性知识(knowledge about)。熟识性知识是指个体在亲身经历世界过程中,获得的对环境机体调整或适应、代表长期的经验累积的一种常识类、非系统性知识;理解性知识则是指那些已经拥有一定精确度、逻辑与概念,对事实和思想已经分类建构成的系统性知识。[4]在帕克的论述中,新闻作为一种公共商品,也是一种知识类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具有链接社群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双重属性。[5]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中的知识分类与罗伯特·帕克比较相似。不过,他反思该书中所用的资料偏重于讨论具有支配性的学术性知识,也就是精英分子的知识,但是较少关注通俗日常的知识。[6]实际上,伯克是依据知识的拥有者或者生产者将知识分为两类的:学术性知识和通俗知识。他还特别辨析“资讯”和“知识”之间的区别:资讯是指相对“生的”、特定的、实际的知识,知识是指经过深思熟虑、处理过的系统化的知识,不过二者并非泾渭分明。[7]除了知识社会学之外,经济学视角也是知识研究中常见的路径,知识被看作一种商品,通过参与经济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构成了“知识经济”。
当今,线上知识形态已与传统知识有很大不同。因此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知识流动的特殊性,还需厘清线上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新特征。新媒体使我们完成了从黄金时段到碎片时间、从固定时空到流动空间的转变,带来了新的传播时空。[8]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下,“今日各式各样的知识在竞相争取我们的注意力,而每一个选择均有其代价”[9],知识消费空间与时间的逐步细分已经成为当前线上知识传播的环境。不仅知识消费的方式在变,知识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中提出了知识的网络化(the 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这一概念。他认为应当把网络理解为可以“无边界”容纳知识的容器,网络化的知识不再确定、固定、令人信赖,却更加人性、透明和包容,更加多元。[10]换言之,在信息超载的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知识本身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
近年来这些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分析知识付费现象,认为知识生产从公共、分享式转变为工业化、专业化生产机制,信息获取从碎片化转变为依赖知识中介。[11]基于“众包”内容生产的线上问答社区,体现了以开放、共享、付费为核心的线上知识传播模式。[12]有学者考察线上知识传播的社会效果,认为线上公开课以及知识社区本质上是一种积极地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13]但也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虽然会使数字鸿沟逐渐缩小,但用户的互联网资本差异与运用差异会产生新的“红利差异”[14]。线上知识传播因信息技术和消费心理因素造成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同样难以忽视。
崔迪系统地总结了当下媒介环境中知识的三个特征:第一是娱乐和知识性信息的混合;第二是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去中心化、去机构化的特征,“知识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任何权威的机构或专家”[15],而是来自“社交网络和同辈群体的内容生产(peer-based content production)”[16];第三则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具有较高合法性和系统性的知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如帕克所定义的熟识性知识,即生活性、实践性的知识。我们可进一步分析,这类知识既不由专业机构生产,甚至也未获得公认的合法性,过去往往依托于地理环境和面对面的具身交流传播与习得,但现在却成为网络知识传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视频社交平台上,人们在线上交流生活、学习、旅游、购物、工作等方面的个人经验,传授本地知识,对他人行动产生影响。
总的来看,线上知识的传播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时空环境的碎片化使得知识本身以及知识的生产和消费都呈现出碎片与细分的特点;其次,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和媒介素养的不同,线上知识产生“红利差异”现象,知识鸿沟并不会简单弥合;最后,线上知识呈现去中心化、多样化的特点,泛生活类知识传播也逐步兴起。
本文所考察的线上“知识”,基于上述关于传统知识的经典分类以及线上知识的新特征而界定,同时为了提供一个操作性的知识定义,本文并不讨论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而是将知识限定在与一般信息(资讯)相区别的范畴。简言之,线上知识指的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对受众产生价值的信息和内容。本研究将线上知识划分为四种类型加以考察:第一,学院知识(即理解性知识,系统性知识);第二,付费知识(即知识经济,作为商品的知识);第三,泛生活类知识(即通俗知识,熟识性知识);第四,新闻知识(链接型知识)。
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空间隔离又为线上知识传播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身体的相对“固定”使许多依赖线下传播的知识空间如学校、书店、博物馆等纷纷上线,更多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必须借助网络完成传收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此类具有高度系统性或专业性的知识是否可以完成“网络化知识”的转变?它们对具身性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不可舍弃?高质量的知识上网是否会进一步推动知识共享、缩小“红利差异”?另一方面,空间的隔离一定意义上使人们的社会时间从碎片回归齐整,那么早前诞生于碎片化消费环境的知识产品是否仍具有吸引力?人们消费知识的方式是否会因时间要素的改变而改变?这些新问题都值得深入考察。
二、具身与围墙:专业知识的流动
(一)具身的重要性
传统教育中的学院知识是具有高系统性的、理解性的知识类型,同时也是对具身性要求较高的知识类型,强调“身份在场”的重要性。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源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它不再沿袭自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之后对意识主体的强调,而是承认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对观念、思想以及行为的形成产生基础而复杂的影响。[17]虽然媒介的发展常常被视为“假肢”和人身体的延伸,但媒介技术发展中对图像、声音,甚至全息交流的追求[18],意味着具身性交流在传播中的不可替代性。学院知识对具身性的强要求体现为系统性知识在传播中受互动性、他律性以及具体知识形式三个因素的影响。
1.互动性
具身认知指出,我们的认知行为是涉身的,认知主体通过躯体、感知器官、视觉系统对周围环境进行体验。[19]学院知识的习得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收双方的感官调动程度,而感官的调动程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有研究指出,学习不是孤立于个体内部的私有过程,而是在社会参与中与他人分享观点、修正观点,并在互动过程中加强理解的过程。[20]因此,在学院知识的线上传授中,能调动更多感官的媒介,会具有更好的表现力。观察发现,不论是直播网课还是录播网课都强调“互动性”以还原或模拟具身性,如要求传收双方都打开摄像头,讨论区与讲授区分割并置,以及课程中预留一定的讨论时间等。
但这三种方式对具身的还原或模拟显然不够。首先是讲授环节,传统课堂中传收双方对彼此在场的“确认”是重要且自然而然的,往往通过躯体和感官加以识别。比如线下“你露出了疑惑的神情,然后他就会慢点讲”(访谈记录:XZ),同时教师也会依据学生的反馈调整讲课的节奏。但是在线上,即使传收双方都打开了摄像头,屏幕的限制也使双方很难同时注意课件与人,身体的缺席使双方在线上空间感觉到“对空言说”,没有感官的反馈也会出现“(老师)会按照他的速度,尽可能快地把内容讲了”,于是听课“会更吃力一点,感觉效果没有在学校好”(访谈记录:XZ)。
其次是讨论环节。令人意外的是,讲授区与讨论区的分割实际上削弱了身体交流中非常重要的“排他性”[21]。区域分割的好处在于,交流反馈信息与传授知识可以在同一时空、同步地进行,二者互不干扰。但是,这也意味着反馈不再具有“打断”的功能,因而丧失了身体交流中的“排他性”,反而使得传收互动性降低了。即使不少课堂会特意安排单独的讨论时间,但由于线上讨论大多以文字为主,将讨论环节与讲授环节分开的做法,仍类似“幽灵性”的交流,不能更好地解决身体缺席的问题。
最后,线上讨论还意味互动性的固定。线下身体在场使人与人的联系相对液态,不会限于固定的空间与时间,存在“流动”的可能。线下课堂学习,“有的课结束了你的问题可以和老师边走边聊”(访谈记录:RD),这种非严肃的讨论有时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补偿,“很有效的一种补充学习的方式”“不是那么严谨反而能启发你更多东西”(访谈记录:RD)。但是线上传收双方在断开连线后就立刻回到相对孤立和隔绝的状态,使知识传播的时间和场景要素变得“固着”了。
2.他律性
具身性还强调身体与环境的嵌入性(embedded)与交互性(interplay),即心智、身体以及环境三者的一体化。[22]线上直播教学过程中,在不开启摄像头的情况下,“虽然有老师讲解的声音,但是因为老师在视觉中的消失会弱化其存在感,感受不到老师与自己之间的交流,在听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访谈记录:ZY)。究其原因,主要是离开线下学习场景的“惯习”后,缺少教学要素的线上空间使个体的学习状态很难长时间保持。具身学习的根植原则(grounded principle)就揭示了学习过程的情境化因素,认为学习过程发生于一定文化环境中,受到情境因素的制约。[23]
传统的教育情境,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纪律的施用意味着一种“惩罚”与“规训”的权力,并且首先是以身体为对象而言的。正如福柯(MichelFoucault)所指出的,“军营、学校、工厂、监狱、疯人院都是现代社会用来驯服个人身体的工具”[24]。按福柯的说法,“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规训权力既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25]在线上教育情境中,纪律的施用同样存在,诸如“摄像头”“点名”和“后台数据”等扮演了“规训”手段的角色。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手段与线下具身性的他律性是有区别的。“(学生作业没交)平时今天就不让你上课,或者罚站,这样起码有一个威慑力,现在(没交作业)你能拿他怎么办?”(访谈记录:CY)
当线上来自学校的“规训”失效以后,“规训”的权力与责任就转交到了学生自己与其家庭身上,“就看家长能不能管理住”(访谈记录:CS)。但显然自我规训与家庭规训是因人而异的。首先是家庭因素,小学的线上教学一般规定“课堂纪律是需要家长在旁边,还有陪同”(访谈记录:BM),这就使得家庭成员的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有造成新的“知识鸿沟”的可能。比如线上学习对电子设备的“硬需求”,数据显示,202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间,天猫打印机成交量同比增长76%;搜索词上,家用学生打印机同比增长16倍。[26]其次是个体自律,线上教学过程中身体相对“自由”,“在听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经常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喝水或做其他的事情”(访谈记录:ZY)。不难发现,自我规训能力较差的学习者,线上学习的实际效果相比线下有下滑的可能。
3.知识形式
并非所有的学院知识都可以成为网课,实践教学的知识因其强具身性的需求,很难在线上流动,即使上网也容易陷入“名存实亡”的困境中。比如,线上体育课受到身体不在场的影响,尽管采用视频打卡的方式上课,但是实际的运动量很难保证。线上教育过程中,体育课的“缺失”带来了负效应,学生反映存在“锻炼的时间不够充足,坐一天比较累”的情况(访谈记录:LA)。高等教育中的实践类知识课程亦是如此。访谈对象RD有一门需要户外行走的课,他说“在实际环境中我们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通过语言或者图片讲述的内容”,这门课在改成以展示图片和PPT的形式之后,“我觉得这门课已经丧失掉灵魂了”(访谈记录:RD)。
在教育领域,人们很早就对于学院知识的线上流动抱有期待。温伯格认为,传统的知识机构创造了如此多的知识,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来是“悲剧”。[27]MOOC被视为是推进教育民主化、知识大众化的创新。为了适应线上注意力难以持续较长时间的特点,MOOC单节课时一般都会较线下的课时更为简短,大多在10到15分钟之间。同时为了增强课程的互动性,MOOC还增添了讨论区。然而研究指出,目前MOOC教育的知识传播方式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如何增强学习体验、提高结业率以及实现学习成果认证,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28]
传统学院知识在线上传播中,身体与环境的嵌入性和交互性的影响是广泛的。访谈的教师对象均谈到,针对线上教学调整了传授的知识内容,“备课的任务是加大了”(访谈记录:CS);互动性的缺失使一节课需要涉及的知识点更加密集,“一个小知识点,就得上网查好多资料”(访谈记录:CY)。对于需要讨论的课堂来说,讨论本身所需要的具身性使得线上教学难以操作,实际上讨论课又变成了传授课。可以推断,线上更适合传授式的知识而非讨论式的知识。但同样需要看到,对于以获取更多知识量为目的的学生而言,网络授课“效率我觉得是提高了”(访谈记录:LA)。如果仅从知识的量和传播效率来看,学院知识的在线流动也有着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知识“围墙”的消解
传统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大多有特定的生产和消费机构,如美术馆、大学、剧院、图书馆等。温伯格认为,诸如大学这样的机构就是把人们放在同一个空间中发展思想,最终界定了知识的标准并让人们相信他们对知识的定义。[29]也就是说,知识机构决定了知识的合法性来源与权威性。福柯认为,这种决定性关系是因为知识的生产和运用是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机构可以抽象为“空间”概念,而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效能。[30]不难发现,当下知识的空间限定与经济利益和权力相关。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空间隔离状态下,往常具有现实“围墙”的知识挣脱了空间束缚,在网上流动起来。中国知网、万方、超星学术等专业性较强的数据库对公众有限放开;不少省市的图书馆、书店、剧院与网络视频直播平台合作,开展免费的线上演播;北京社戏控股与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合作举办了“宅现场戏剧节”,连续一周轮播戏剧;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还举办了多场“线上艺术生活”和“云端见面会”;一些书店、出版社联合学者举办云端读书分享会。过去需要与网络平台竞争生存空间的线下知识场所,在新冠肺炎期间反而更多地与网络平台合作,知识在网络上的流动也更加显著。相比于系统性的、理解性的学院知识,专业机构提供的知识虽具有一定“门槛”,但碎片化的形式更便于其流动。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此类知识因由专业机构生产和筛选,在信息超载的传播环境下也更易获得青睐。
知识的线上流动并不一定以机构的消失为代价。网络并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网络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机构。同时,这类网络机构也大多追寻对所贡献知识收费的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利益的基础。[31]比如电子书、会员付费等知识付费产品,在线上流动中就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不过即便如此,疫情隔离期间大多数知识都选择了免费流动。整体来讲,这种知识的流动显然是暂时的,当空间隔离结束、社会恢复常态后,这些知识就会撤回到固有的空间领域中,继续成为机构获取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基础。
不过,疫情隔离期间看上去“乌托邦”式的知识共享与流动是否为我们指明了线上知识传播的未来呢?过去将知识固定于特定的空间中,造就了文学、艺术和思想上的经典和流派,但大众难以进入这一知识空间,实际上也造成了回声室效应[32]。如果知识拥抱网络,就可能跨越地理和空间距离的障碍,知识变得更容易获得。进一步讲,互联网上优质的、专业的知识越多,无论是否存在线上付费的“门槛”,都会在整体上提升线上知识的可靠程度和可接近性。
三、媒介的偏向:知识消费的惯习及其改变
伊尼斯(Harold Innis)认为,媒介是有偏向的。“传媒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33]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再到网络传播时代,承载知识的媒介所具有的偏向性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消费知识的方式和能力。温伯格指出,互联网缩短了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知识的网络化正在给知识的本质以及形成于书籍阅读的长形式思考(long-form thought)[34]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一)音频与碎片化的知识付费
一般认为,知识付费产品(狭义的知识付费概念)诞生于信息超载和知识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在信息极端充裕的环境下,当求知被建立为一种规范(norm),它就同时带来动力和焦虑。[35]因此,相较于上文所论述的学院知识,知识付费的内容更加垂直,在人们的一般经验中具有高场景度、高可操作性。[36]
在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演变划分中,口语传播时代人们具身性的交流使其成为一个听觉偏向的时代。[37]音频媒介因主要为口语传播,更具人情味和贴近感,同时又不像视频一样需要投入更多的感官。因此,付费类知识往往以音频的形式呈现,时长较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快餐式、碎片化的轻知识”[38]。其消费场景也是碎片化的,不需要人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系统性地学习,[39]而是出现在听觉可以独立于视觉或者其他身体劳动之外的场景之中。
疫情隔离期间,人们的社会时间安排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如郑作彧指出,社会时间是一种通过对诸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加以协调,使行动者彼此的行动交织,能依其意向在需要的时间点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40]由于节省了通勤的时间,缺乏具身性的在场改变了人们社会时间的参照机制,“在家的时间更加完整”(访谈记录:LA)。但个体时间重新从碎片回归齐整并没有使长阅读完全代替碎片化的知识消费。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人们对以音频为主要载体的知识消费并未减少,反而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分析发现,诸如喜马拉雅、蜻蜓FM、苹果Podcast等平台均在疫情隔离期间新增了许多播客节目。音频形式的知识既耗费较少的注意力,同时效果也不错,“我可以听到相对时新的(信息),比起自己去混杂地获取,这些知识还经过高效高质的讲解”(访谈记录:ZY)。但使用者仍然会以一种碎片化和随意的方式收听互联网音频,如从过去“回家的路上”变为了“和妈妈一起做运动的时候听”(访谈记录:ZY),或者“看书也好,打游戏好,我就把它在那边像背景音一样放着,反而会舒服很多”(访谈记录:RD)。
使用者对待互联网音频媒介中知识的态度是随意的,对获得知识的预期值较低,只是消费场景仍然是碎片化和伴随式的。在疫情隔离期间,知识付费行为一定程度上同样受限于音频媒介的特性,即“知识的密集度没那么高”(访谈记录:RD)。因此,使用者更像是一种“游牧”的姿态,“听到感兴趣的会在手机上记下来几个字、几句话”(访谈记录:ZY),但是“如果错过了,我就会觉得错过就错过了吧”(访谈记录:RD)。
一项针对得到、英语流利说、知乎、喜马拉雅等知识付费平台用户的调查显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2月),有63.1%的中国用户(在线学习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音频媒介为载体的付费类知识消费的增多,并不一定代表知识付费产品的流动增多。访谈发现,对于那些以前使用过知识付费产品而后来又放弃的用户来说,疫情隔离期间新增的收听习惯更多是免费的内容。原因在于,切割的碎片化的知识信息量并不像系统知识那么密集,伴随式的消费场景又导致在知识获取上信息量的再一次削弱,因此就容易出现“付了快200买了一个年度会员,就是想上面的好多可以读,但是一年过去了,我好像也就真的看过了一两本书……我觉得那就太不值了,就还不如我直接去买书”(访谈记录:XY)的状况。此外,目前知识付费平台质量的不稳定以及付费环境尚未完全成熟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推测,当非常态的“时空环境”回归常态时,付费类知识的流动仍然取决于提供的知识质量,线上的知识经济如何实现“机构化”,树立起权威性和合法性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在线书籍知识传播
疫情期间,源于书籍媒介形成的长形式思考和系统性知识的获取出现了增长。这反映了知识消费习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微信战“疫”数据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微信读书用户阅读量提升,每百人比上个月平均多读110本书。[42]其主题集中于医疗和疫情相关的知识,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鼠疫》《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等。
受访者同样表示居家时间增加后,“在家太无聊了,之前看到有同学在用微信读书,就试了一下”,“自己的阅读量极大地增加了”(访谈记录:XZ)。线上读书App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物流停滞和图书馆等场所关闭所带来的纸质书的“稀缺”,使系统性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易得。
实际上,系统性阅读更多作为对抗碎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出现。疫情隔离期间,由于网上流动的信息量增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医学健康类新闻,以非常碎片化的形态充斥网络,“牵扯出来的方面太多了,不是一个系统的、有框架有逻辑的事”(访谈记录:RD)。在个体时间相对完整的情况下,系统性阅读可以帮助抵抗碎片知识的烦恼,“看书,好像是为了把这个碎片化的东西装到哪去那种感觉,把它拼凑一下”(访谈记录:XZ)。
总之,疫情期间的空间隔离使个体碎片化的时间重归齐整,碎片化场景的消失一方面并没有使碎片化的知识消费减少,另一方面使得系统化的知识获取行为增多。看起来,每一种形式都加强了与自己“忠实用户”之间的联系,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变节者”,仍需要依靠翔实的实证数据来分析。
四、权威知识节点:作为知识的疫情新闻信息
从知识流动的角度,作为知识的疫情新闻信息是丰富且倾向于均匀的。知识沟理论指出,当某些事件引发媒体大量报道的时候,媒介环境中相关的信息就会急剧丰富而接近饱和的状态,知识沟减少甚至弥合而出现“天花板效应”(the ceiling effect)。但是,网上信息的过度饱和也可能使信息的可信度降低,信息在快速流动的同时,“无形状的知识反映了知识的更新,但却以消弭了中央权威为代价”[43]。知识与噪音混杂在一起,加之知识的“未决性”特征,有价值的知识反而更难获得了。
为了应对上述知识危机,传统新闻媒体机构拆掉了“知识”的围墙,为知识的进一步流动“减负”。如《财新》限时取消了付费墙,使高质量的疫情报道更易得。此外,传统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寻找网上流动的新途径,如央视新闻不仅在传统的电视媒介中滚动播放,更重要的是跨平台分享信息,24小时不间断直播,让疫情相关的新闻知识充分流动起来。就网络化的、不再拥有边界的知识而言,权威机构仍然是一个“停止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停止点”的话,我们就无法到达任何地方,[44]新闻知识就无法得以确证。
除了传统的新闻媒体,知识类平台也开始与传统的知识机构合作。前者提供知识流动的渠道和接入口,后者提供知识的权威和合法性来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相应的防疫知识。比如,得到App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等合作,出版了疫情防护电子书。[45]
在以上两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与疫情相关的权威性知识在网络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均匀的状态。在线上流动过程中,这些知识也嵌入讨论和协商的网络体系中,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不同的网络平台上,以节点的形态与彼此链接,在多元的媒介形态和渠道中与使用者保持“触手可及”的距离。
较为均匀流动的除了疫情相关的新闻知识,还有泛知识,也即前文所述的第三种知识类型—“熟识性知识”。疫情期间的空间隔离政策使公众经历着彼此类似的生活环境,空间环境的相似以及生活时间节奏的同步,一定程度上使生活类、本地化知识的分享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可能。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以及淘宝、小红书等购物平台上,广泛流动着诸如“电饭煲蛋糕”等日常生活的熟识性知识,这也成为疫情期间一种很有意思的传播现象。
五、结论与讨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空间隔离的时空环境下,知识在线上的流动是暂时的、非常态的,但却提供了一块特殊的考察“田野”。我们也得以更深入地考察线上知识是如何流动、人们获得的信息呈现何种形态以及线上知识传播之于个体与社会的意义等问题。研究初步发现,线上知识的流动呈现如下面貌与特点:
第一,对专业的、系统的、理解性的学院知识类型而言,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具身性传播仍不可或缺。具身性可以保证知识传收过程中的互动性、他律性和不同知识类型的实现,保障知识传播的有效性。同样,线上教学更适合传授式的知识而非讨论式的知识,规训权力和责任从学校向家庭转移容易导致新的知识鸿沟的出现。对于由专业知识机构所生产的知识而言,空间性是知识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来源,然而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的线上实践,让我们有理由想象一个更加开放的、知识共享的未来。
第二,媒介的偏向决定了知识如何选择流动时的媒介载体,但是“游牧”式获取碎片化知识或已成为知识消费的“惯习”,短时间内的时空变化并不会引发知识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一定程度上讲,系统化的知识习得仍是我们抵抗信息超载与知识危机的重要方式。
第三,知识的重要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它在网络中的分布状态,相对重要的知识即使在区隔的网络空间中也会均匀地流动。同时,即使知识的网络化使知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减弱,网络中依旧会形成新的权威性知识节点,成为人们在网络化知识中的“停靠点”,知识得以被确证,并为个体的行动提供意义。
空间隔离改变了知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间接地影响了个体的社会时间,但是每一位用户、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机构、知识的媒介载体以及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视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中的行动者。在这张巨大的网中,“任何既定的社会现实都是一系列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46]。但显然,完全抛弃经济利益和由权力带来的知识权威性与合法性是不现实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围墙”作为网络知识之海中停靠的“节点”。然而应看到,虽然知识的流动摆脱不了知识权力和知识经济的“枷锁”,但在一个优质信息越多的网络环境中,知识的整体质量就会越高,知识也更易得,我们就更可能走向知识而不是走向无知。
注释:
[1]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M].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71-73.
[2]孙明哲.后期维特根斯坦与知识的社会性——论D.布鲁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社会学解读[J].世界哲学,2019(05):124-131.
[3]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M].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
[4]PARK R E.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5):669-686.
[5]郑忠明.思想的缺席:罗伯特•E.帕克与“李普曼—杜威争论”——打捞传播的知识社会学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7):54-71+127.
[6][7][9]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M].贾仕蘅,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46,42,43.
[8]彭兰.新媒体传播:新图景与新机理[J].新闻与写作,2018(7):5-11.
[10][27][29][31][32][34][43][44]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2,296,294,295,295,147,173,278.
[11]马澈,穆天阳.一种新的互联网知识传播范式:“知识付费”的逻辑与反思[J].新闻与写作,2018(4):40-47.
[12]邹伯涵,罗浩.知识付费——以开放、共享、付费为核心的知识传播模式[J].新媒体研究,2017,3(11):110-112+132.
[13]徐小龙,王方华.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机制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08):83-86.
[14]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许英康.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15][16]崔迪.媒介知识:传播学视野下的知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27,25.
[17][22]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2):80-89.
[18][21]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40(2):37-46.
[19]刘晓力.交互隐喻与涉身哲学——认知科学新进路的哲学基础[J].哲学研究,2005(10):74-81+130.
[20][23]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教育研究,2015,36(04):104-114.
[24]杨大春.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4):116-123.
[25]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67,200.
[26]朱银玲.宅家上网课家用打印机成风口[N/OL].(2020-03-20).http://education.news.cn/2020-03/20/c_1210522158.htm.
[28]袁松鹤,刘选.中国大学MOOC实践现状及共有问题——来自中国大学MOOC实践报告[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04):3-12+22.
[30]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25(05):167-191+245.
[33]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17
[35]崔迪.媒介知识:传播学视野下的知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10
[36]喻国明,郭超凯.线上知识付费:主要类型、形态架构与发展模式[J].编辑学刊,2017(5):6-11.
[37]田园.听觉生态位的超越:从广播媒体到听觉媒体[J].当代传播,2018(3):60-62+78.
[38][39]徐敬宏,程雪梅,胡世明.知识付费发展现状、问题与趋势[J].编辑之友,2018(5):13-16.
[40]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23.
[41]艾媒网.知识付费行业:市场规模达278亿,贩卖焦虑成困境,疫情带来机遇[N/OL].(2020-02-23).https://www.iimedia.cn/c460/69261.html.
[42]微信发布《微信战“疫”数据报告》[N/OL].(2020-02-18).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20/0218/c1007-31592060.html.
[45]疫情期间“拉新”红利显著知识付费如何保住战果[N/OL].(2020-03-24).http://news.cctv.com/2020/03/24/ARTIJNHsd91c
kCW4Bf4GcL6X200324.shtml?spm=C94212.P4YnMod9m2uD.ENPMkWvfnaiV.100.
[46]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41(4):6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