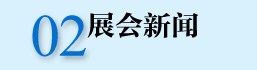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郑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摘 要】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新型支柱,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播战略意义。网络文学的繁荣离不开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但网络文学"作者-网络-读者"三位一体的特殊生产机制也给基于"作者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生产逻辑与"消费性-转换性"使用者二元假设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带来适用困境。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不应只考虑网络文学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同时也要兼顾使用者参与、交流和创造性表达的诉求,通过在合理使用规定中引入兜底条款维护作者-读者合作共创空间、防止滥用技术措施保障创作-传播知识共享机制,以期在知识的共创与共享中促进知识繁荣。
【关键词】网络文学;使用者;著作权限制;知识共创;知识共享
我们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用电脑进行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1],伴随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而崛起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形成拥有1755万创作者群体以及4.55亿读者群体的庞大体量,涵盖都市、历史、游戏等二十余个大类型,二百余种小分类的“多元化”创新文化,除历史、言情、穿越等成熟类型作品以外,还新增二次元、体育、科幻类型作品。在网络IP全产业链条开发与粉丝用户文化创建背景下,网络文学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而且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文出海”过程中承担着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传播战略意义。[2]
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但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生产的特殊性也给著作权法维持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平衡机制带来新的挑战。互联网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而且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与传播机制。互联网取消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出版流程,把作者创作与读者互动压缩在即时性的时空平面内,作者与读者的合作从阅读阶段上升到写作过程,从文本解读进入到文本生产。[3]互联网技术对文学生产的渗透,籍由网络文学为载体,催生出新型使用者群体,给基于传统文学生产逻辑与使用者二元假设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带来适用困境的同时,也蕴藏着变革契机。
一、网络文学催生新型使用者
文化作为一种群体生活方式与趋于稳定的集体性共同反映,是由无数个体经验在交互影响过程中沉淀、定型而成的整体经验与共同观念。[4]文化形态变迁深受媒介技术的影响,新媒介技术通过创造新传播方式,形成新社群共同体,带来利益结构、符号体系、社会性质等变化从而催生文化形态的变迁。[5]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技术时代的新文学,是全球性自由文化浪潮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催生出以参与、交流和创造性表达为特征的新型使用者群体。
(一)网络技术时代的新文学
网络文学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互联网媒介技术的演进轨迹。从媒体传播角度,我国互联网技术经历了从Web1.0到Web3.0的发展阶段:1999—2004年是以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为代表的Web1.0阶段;2005—2009年是以博客、播客为代表的Web2.0阶段;2010年至今是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Web3.0阶段。[6]随着互联网技术由Web1.0更迭为Web3.0,移动、去中心微式传播,动态、开放式网络结构,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分享与深度参与的多向互动传播。[7]在此过程中,文学与互联网逐步结合,形成以数字化特点呈现的新型文学生产方式。
在Web1.0时代,全球海量信息经由互联网向使用者提供,内容传播与信息检索是这一网络泛传播时期的主要特征。互联网媒介技术犹如神奇的魔法棒,将各类文化行为简化为所有参与者掌握的数字符号,文化生产机制各环节,从创作、出版到衍生文化产品,均呈现出彻底去中心化特征。[8]数字技术降低了写作门槛与传播成本,“互相关联的语言比特”创造出具有“超文本性”与“高虚拟性”的数字文学。[9]“榕树下”等原创文学网站成为写作者们发布作品、与读者进行即时沟通交流的虚拟社交场所。
伴随多元媒介融合的Web2.0时代,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信息传播形成“个体创造—群体协作”的网络社会结构。[10]在Web1.0中作为终端的使用者成为了Web2.0网络循环中的一环,使用者不再是互联网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传播者;不再是单纯的互联网信息浏览者,而是成为内容生产者与提供者。随着网络社区、视频分享、博客、播客等网站纷纷采用“使用者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的架构,信息传播的单向性被突破。在“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红袖添香”等文学站点,原创作品不再是作者单方面自抒胸臆,而是作者与读者交流互动的产物,读者点击量的高低成为衡量作品市场反馈的直接标准,读者付费阅读成为支撑作者创作与文学网站运营的经济基础。
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互联网媒介技术的Web3.0时代,信息传播更加智能化,网络文学商业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随着资本的引入,网络小说被孵化出一系列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衍生文化产品,网络文学逐渐成为新型文化创意源头,在全球文化工业链条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内容生产任务。
(二)自由文化浪潮的新群体
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言,比特作为信息时代新世界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11]互联网媒介技术在改变信息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同时,信息使用者的身份与角色也随之悄然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架构掀起了全球性自由文化浪潮,互联网和其他技术进步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新范式,任何人都能依靠自身价值成为文化参与者。在自由文化运动典型代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倡导者斯坦福大学劳伦斯·莱斯格教授看来,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中的“自由”并不是“免费啤酒”中的“免费”的意思,而是“言论自由”与“意思自治”。自由文化旨在支持和保护创作者与革新者,反对创作者进行创作必须先经过权利人或先前作者许可的“许可文化”(permission culture),但自由文化并不意味着废除著作权(copyleft)的激进文化,犹如自由市场并不意味着免费市场一样。[12]自由文化运动背后的动因在于使用者渴望挣脱著作权人的扼制与束缚,追求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
在文学领域,传统印刷媒介所塑造的精英文化与正统文学体制的话语霸权被网络技术所打破,底层草根“屁民”在网络平台所发出的民间声音,奏响了大众文学形态的网络文学乐章。[13]随着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消费全过程都在网络上完成,网络文学逐渐定型为消费引导生产的商业化“类型文学”。其中,作品类型化、读者参与创作成为网络文学生产的基本特征。如同象棋对弈的既定游戏规则,网络文学亦存在着潜在故事结构或套路的“设定”。以网络奇幻小说为例,作者在创作之前往往会先在文学网站讨论区发帖,将自己构思的魔法世界设定与网友交流,在相互讨论争辩中不断修正设定的合理性。尽管作者有决定是否在小说中引入魔法社会,魔法社会是否区分低魔、中魔、高魔的自由,但一旦作者决定引入魔法社会这一设定,其运行规则就不能由作者肆意发挥,而要受到先前经典奇幻小说设定的“规则书”限制及读者经验所形成的有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观限制。[14]如果说传统小说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系由作者单方面邀请读者进入已经完成的世界,“小说从卷首语开始,就在乞求被阅读,就在告诉我们,它愿意怎样被阅读,在暗示我们可能会寻觅到什么”[15],那么网络小说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则由阅读阶段上升为创作阶段。作者和读者的讨论交流,共同构建网络小说“设定”、推动网络小说的“类型”进化。[16]
互联网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者越来越不愿意充当等待填鸭式喂养的观众,他们相信文化是双向性的,包括积极参与,而不仅仅是被动消费;他们不再满足于作为单向媒体的终端用户,而是追求交流的自治,同时希望其接触作品的权利得到保障;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欲望,不仅阅读和欣赏,而且重组和混搭。网络文学读者代表了互联网环境下重视参与、交流与表达的新型使用者群体。约瑟夫·刘将其称之为积极消费者(active consumer)[17]、尼瓦·科伦将其表述为参与型消费者(consumer-participant)[18]、朱莉·科恩则将其视为情境化使用者(situated user)[19]。网络文学读者所代表的新型使用者群体“通过从消费到创造性游戏等各种行为而参与到其文化语境提供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中去”,主要基于四种目的而使用文化产品:消费、交流、自我发展与创造性表达。[20]
二、网络文学使用者超越使用者二元假设
互联网媒介技术虽然催生出网络文学和新型使用者群体,然而现实却如哈佛大学乔纳森·齐特林教授所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尽管给予业余爱好者们强大工具通过截取大众文化片段去制造和分享有趣的、有用的和有益社会的表达,而现行著作权法中却没有空间容纳这一重要的文化突变。[21]究其根源在于著作权法上有较为发达的作者观念与保护体系,而对作品的使用者却鲜有研究,这不仅体现在著作权法使用者的缺位现象上,而且反映于学者们对使用者的认识分歧中。基于“作者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生产想象,著作权法形成了“消费性—转换性”使用者二元假设。网络文学“读者参与创作”的特殊生产机制孕育了新型使用者群体,成为超越二元假设的“第三种使用者”。
(一)使用者缺位与认识分歧
在“作者中心主义”文学生产观的影响下,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存在着使用者缺位现象,除却以公共利益形态的抽象认识以外,著作权法并未对使用者利益加以明确规定或细化,甚至未曾采用统一指称作品使用主体的一般术语。不仅“使用者”一词在我国《著作权法》中难见踪影,欧盟自1999年所通过的多项著作权相关指令也从未提及“使用者”字眼。[22]美国立法亦是如此,美国《版权法》多次提及“作者”(authors)和“版权人”(copyright owners),但对于获得并使用作品的相对方却没有一以贯之的称谓,而是在不同场合将其称之为“人们”(persons)、“公众”(the public)、复制件“所有人”(“owner”of a copy)、“传输接收者”(transmission recipient)、“用户”(subscriber)或“消费者”(consumer)。
与此同时,学术界形形色色的作品使用者称谓也反映了学者们的认识分歧。作品使用者或从广义中性意义层面被泛化为“人们”(persons)、“公民”(people)、“公众”(public)、“个人”(individuals)等,或从狭义消费属性层面被描述为“消费者”(consumers)、“终端用户”(enduser)、“观众”(audience)、“粉丝”(fans)等。其中,“消费者”术语为诸多学者所偏好。约瑟夫·刘在解释这种偏好时认为“消费者”一词较之“公众”等其他更为中性的术语,更能突出对作品的消费属性。[23]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消费者”一词实质上存在误导性,从概念上不适合指称人类接收文化产品以及与其生发的互动关系。[24]由于消费带有浪费、耗尽的负面意义,消费者想象并不符合人类对信息作品的使用。人们并不像消费一块巧克力那样消费一本书,或许阅读书籍和吃巧克力都能够带来愉悦,但是包含在书籍中的受著作权保护的信息并没有被消耗。[25]信息作品永远不会像其他有形商品一样被耗尽,“内容生产产业最大的阴谋在于力图使人们相信读者和听众是‘消费者’,如同咽下糖果一样吃掉字词”[26]。鉴于此,“使用者”(users)被越来越多学者视为比“消费者”更适合当前著作权制度。正如朱莉·科恩所言,“使用者”一词同时包含在文化过程中沉溺的消费以及更为积极的参与,体现了使用者在著作权制度中发挥的两种功能,“使用者接收作品,而且(部分)使用者成为作者”[27]。
(二)使用者二元假设
传统著作权法对于使用者的制度想象正是基于“使用者接收作品”与“使用者成为作者”的二元假设。由此,著作权法上的使用者分别以消费性使用者(consumptive user)与转换性使用者(transformative user)两种类型的形象出现。
消费性使用者是被动的消费者,依据需求、用途和价格来购买文化商品。从某种意义上,消费性使用者同普通消费者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将著作权作品当作休闲娱乐商品,阅读书籍、观看电影、聆听音乐,这种被动消费同消费土豆片、汽水、运动鞋及其他物质商品并没有显著不同。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消费性使用者一直游离于著作权法旨在“促进创作”的生产性氛围之外,除了提供作品终端市场以及自私地消费他人创造物以外,他们在著作权法中没有地位,也无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目标。[28]针对这部分使用者,著作权法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有充足的作品供其消费。为此,著作权法关注的重心是如何通过赋予作者独占性权利以激励作者继续创作,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作品。只要作品形态的文化商品源源不断地提供到市场上,至于文化商品购买者的利益,似乎不是著作权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相反,为了保障作者获得足够的创作激励,消费性使用者应当付费使用作品。尤其是随着作品在互联网上创作与传播,作者理应获得更大的权利来控制这部分使用者接触作品并收取费用。
与消费性使用者相比,转换性使用者并不是被动、消极地消费,而是通过消化、吸收、重组,进而创造出新作品,成为作者。事实上,作者经常在创作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消费先前的作品。没有任何作品是真正全新的,“所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既有作品基础之上的”[29]。任何作品的创作与其说是像从海水的泡沫里诞生的爱神阿芙罗狄蒂,不如说更倾向于一种转化和重组。[30]从此种意义上而言,所有作者同时是先前作品的消费者。因此,作为生产性使用者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有权获得著作权法上的某些特权。这部分使用者的利益,目前已经在著作权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著作权法通过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演绎作品以及合理使用制度明确承认了在先作者和在后作者的纽带关系。在后作者可以付费获得在先作品,吸取其中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而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作品;甚至还可以以个人学习和研究为目的,不经在先作者许可也不需付费而进行合理使用。
(三)网络文学“第三种使用者”
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基于传统文学生产“作者—读者”关系想象而形成的消费性使用者与转换性使用者二元假设,正被网络文学“作者—网络—读者”三位一体的生产机制所打破。网络文学读者所代表的互联网使用者群体,正是无法归入传统著作权法上使用者二元假设范畴的所谓“第三种使用者”,即强调自治、交流和创造性表达的积极使用者(active user)。[31]
与消费性使用者不同,网络文学使用者不满足于被动、消极地消费作品,而是主动、积极地参与作品创作以及表达意愿。借助互联网媒介技术,网络文学使用者通过与作者在线互动参与作品创作,通过点击、付费、打赏、追星反映消费需求,成为影响作者创作倾向的风向标。
与转换性使用者对作品的使用旨在创作出新的作品进而成为新的作者不同,网络文学使用者参与创作纯粹出于一种兴趣爱好与表达欲望。他们不是以写作为生的职业创作者,而是对写作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虽然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作者,但由于著作权法对于作者准入资格有较高要求,只有具备独创性的作品创作者才能被称之为作者。而对于绝大部分业余爱好者而言,其表达虽可能具有某种个体创造性,但由于程度太过式微不符合独创性要求,因而无法像转换性使用者一样取得作者身份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三、网络文学使用者面临著作权限制适用困境
现行著作权法的权利与权利限制配置体系是基于传统技术与文学生产想象而形成的。天才作家与消费性—转换性使用者的划分构成著作权权利制度与权利限制制度的分水岭。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通过对著作权人专有权利行使进行制约,体现了对作者以外使用者等社会公众利益的兼顾。当互联网媒介技术渗入文学生产过程、改变作者—读者关系、赋权作品使用者参与作品创作时,基于使用者二元假设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缺乏网络文学使用者的适用空间。一方面,合理使用制度倾向于强调转换性使用,排斥网络文学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另一方面,文学网站采取技术措施控制作品访问,筑起网络文学使用者接触作品的数字藩篱。
(一)合理使用转换性倾向排斥网络文学使用者
合理使用制度因允许使用者在法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对作品进行免费使用,而被视为是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中对著作权人限制程度最大,最能体现使用者利益的平衡机制。合理使用制度在许可机制之外构建了非侵权性使用的法定规则,为使用者保留了自由无偿使用作品的公共空间,有助于实现著作权法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促进文化科学发展与繁荣的立法宗旨。[32]
从立法体例上,我国《著作权法》采取了封闭列举式,第22条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情形。其中,与使用者使用作品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1项所规定的个人使用限制,允许使用者“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自由免费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然而,随着合理使用规则越来越倾向于强调“转换性使用”,使用者的自由空间也相应缩限。“给原作增添了价值,将引用原作作为原材料,进而将其转化以创造出新的信息、新的美感、新的洞见与新的内涵”的转换性使用属于典型的再创作行为,因被认为符合合理使用制度所要保护的根本价值,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作、促进全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的立法目标而受到重视。[33]与之相反,“个人欣赏”目的的使用行为因不具有生产性而被英国、德国等国排斥于合理使用范畴之外。
尽管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条款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转换性使用要求,但是在第三次修改过程中,针对使用者个人使用作品情形,《〈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43条第1款第1项将《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中“欣赏”这一消费性使用排除,仅保留具有转换性使用性质的“学习、研究”,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合理使用规则强调转换性使用的趋势。除此以外,为解决我国封闭列举式合理使用规定所列类型不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不乏部分法院审判裁决时直接引入美国法官造法产物的转换性使用作为认定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34]合理使用制度的转换性使用门槛使得只有做出生产性贡献,即必须将所引用材料以与原作不同方式或不同目的进行使用的转换性使用者才能获得无偿使用作品的自由,而非转换性的使用则被排斥在外。其消极影响在于网络文学使用者所重视和强调的交流、讨论、参与等非转换性使用将得不到保障,而这些行为同样是使用者自我表达、言论自由和参与文化的重要形式。
(二)技术措施限制网络文学使用者接触作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共空间。在文学生产领域,互联网技术所提供的公共空间以汇聚众多网络小说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的文学网站形式出现。在文学网站场域的类型化主题板块下,作者—读者通过即时互动形成具有共生关系的合作生产系统,为网络文学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网络文学生产公共空间的文学网站既是内容生产车间与内容提供平台,同时也是追求利润、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商业实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唐家三少”“天下归元”“爱潜水的乌贼”等“大神”作者及其作品成为文学网站竞相争夺的首要“资源”。当资本渗入网络文学生产之中,热门网络文学作者成为网站签约作家,从作者—读者共生关系的合作生产系统中被剥离出来,通过既有著作权法律制度赋予的独占权利以及互联网媒介提供的访问限制技术措施,重新筑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数字鸿沟。
随着文学网站纷纷引入VIP付费阅读机制,读者的参与度被消费力所度量,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读者可以获取网站评选每月优秀作品的“月票”,消费力最强的一部分读者成为读者群体中的“盟主”,不仅拥有领导其他“粉丝们”为作者贡献“点击量”“推荐”和“打赏”的话语权,而且作为普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而特别受到作者优待,甚至名字被作者写入网络小说。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未付费读者群体则由于缺乏金钱消费,被隔离于付费章节所代表的网络文学精华部分营造的文化公共空间之外。这部分未付费读者,可能对于网络文学的兴趣与参与意愿丝毫不逊于付费读者,却被金钱消费入场券挡在了门外。倘若愿意付费或付得起费的人能够接触作品,不愿付费或付不起费的人则被排除在外,文化领域将可能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35]诚然“随着大众传媒广泛普及以及信息传播量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速度获取更多信息”[36],但以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与消费力大小来决定知识获取多寡,有违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和谐社会民主文化。
四、共创与共享:网络文学著作权限制的变革契机
我国著作权法作为参鉴域外经验的制度产物,既有英美法系痕迹,也有大陆法系烙印。[37]当我们企图运用18世纪诞生于遥远英国、[38]基于“作者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生产逻辑所构建的著作权法基本原则以及使用者二元假设,来继续支配21世纪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关系时,势必面临制度错位与适用困境。但危机与机遇总是相伴而生,制度困境中往往蕴藏着变革契机。在网络文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之下,变革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一)网络文学著作权限制变革的必要性
互联网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而且塑造了制度变革的社会力量。从国家—社会视角,互联网技术在现实时空之外塑造虚拟公共空间,成为积聚网民认同,进而形成对国家产生影响性社会行动力量的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市民社会。[39]抛开国家—社会视角,仅就互联网本身的社会意义而言,互联网犹如庞大无边的虚拟城市,网民在线上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消费方式逐渐衍生出新的自我认同与参与诉求,形成现实社会之外影响未来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社会力量。[40]
在文学网站所提供的虚拟文化公共空间中,网络文学生产的参与者不仅有妙手生花的作家,还有以互联网原住民身份存在的“网生代”读者。作者—网站—读者三位一体的网络文学生态体系里,网络小说读者不再满足于被动等待作者提供精神食粮,而是以交流者、评论者,甚至批评者的积极使用者形象参与网络文学“设定”的构建与“类型”的演化。借用托马斯·麦克拉夫林将“土著理论”运用于大众消费行为的分析范式,如同美国黑人文化中的布鲁斯音乐体现了缺乏文化权力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自己的文化批评体系,大众消费行为亦具有“去精英化”倾向的文化批评意义。[41]网络文学正是基于“网生代”积极使用者们以批评者的身份参与文学生产,才形成了传统精英“正统”文学之外的大众平民文学。倘若脱离“大众”,作为大众平民文学的网络文学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此种意义上而言,著作权法如何从制度层面对网络文学著作权进行限制,保障使用者在互联网文学生产共创空间的表达自由和参与自由,是维持网络文学继续保持旺盛生命力,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加大网络文学作者著作权保护力度,对“洗稿”“融梗”等抄袭行为予以惩处,对危及文学网站、衍生影视游戏产业的盗版行为予以制裁;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资本逐利本质下,文学网站滥用技术措施控制作品接触,用金钱消费限定读者参与自由的商业模式对网络文学生产本身的破坏。
(二)网络文学著作权限制的改革措施
与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彻底批判作者对作品的支配地位,认为读者诞生的代价就是作者之死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不同,[42]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平衡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关系,并非旨在单方面否定作者、肯定读者,而是强调顺应作者—读者互动、读者参与作者创作,双方共同推动“类型”进化的新型文学生产机制。在网络文学领域,未来我国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制度变革应着眼于妥善处理作者与读者、独占与共享的关系,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措施。
1.合理使用引入兜底条款维护作者—读者合作共创空间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系沿袭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为确保法律确定性与可预见性而采取封闭列举式合理使用立法。为解决所列举类型过窄、滞后于新技术发展需求的缺陷,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43条第1款增加第(十三)项“其他情形”的开放性兜底规定。兜底条款的引入具有合理性,不仅可以实现立法弹性,为实施特定产业政策、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的等预留一定空间,[43]而且可以矫正合理使用规则强调转换性使用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可以以公共政策为导向,从促进言论自由与表达、促进学习、促进信息接触、鼓励文化创新、保护隐私、保护使用者自治权等目的,[44]来探索网络文学使用者的合理使用适用情形。与此同时,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对于网络文学产业领域司法审判所创设的新型合理使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梳理,在此基础上出台司法解释,进而明确网络文学使用者的哪些使用行为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其他情形”。只有确保网络文学使用者参与、交流与表达行为的合法性,保留合理使用适用空间,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网络文学作者—读者社群合作生产机制。
2.防止滥用技术措施保障创作—传播知识共享机制
网络文学使用者参与创作的前提是接触作品,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却没有顾及使用者的接触权利。《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未经许可,故意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构成著作权侵权,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和第7条所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情形以及第12条所列允许规避技术措施情形均不包括使用者对作品的个人使用行为。这就意味着,一旦网络文学著作权人以及文学网站采取访问限制技术措施,使用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行规避,否则构成著作权侵权。
从商业运营角度,技术措施固然为打击盗版、付费阅读、粉丝经济变现提供了有力手段,但是从网络文学生产角度,技术措施藩篱下金钱消费决定读者参与、经济地位决定知识地位的文化马太效应一旦加剧,在使用者群体中横亘起的数字鸿沟将成为网络文学生产的消解力量。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虽离不开技术措施,但是应当避免著作权借助技术措施进行“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数字扩张,[45]防止技术措施被滥用从而危害网络文学自身发展。
为此,应将采取技术措施严格限定于保护著作权的必要范围,如果与著作权保护无关或超出著作权保护范围,比如用于公有领域作品及不构成作品的材料,或者阻止合理使用行为,则该技术措施被视为无效。实践中,可以依据公共政策目的与产业政策,通过出台司法解释以及法官个案裁决,动态监测技术措施是否存在滥用。当网络文学使用者参与、交流与表达自由受到不当阻碍时,只有通过否定技术措施的有效性从而排斥其受到反规避规则的法律保护,才能保障创作—传播知识共享机制不被破坏。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华盛顿所言,知识在任何国家都是公众幸福的基石。互联网媒介技术所孕育的网络文学不仅是资本盛宴中的新型文化创意源头与网络IP全产业链条中的内容生产环节,更是融入无数网络文学使用者智慧与表达的大众平民文学生态。新时代下,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不应只考虑网络文学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同时也要兼顾使用者参与、交流和创造性表达的诉求,以期在知识的共创与共享中促进知识繁荣。
参考文献
[1] 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本体论[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R]. 2020-02-18.
[3] 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
[4]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 [M]. 高晓玲,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11.
[5]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25.
[6] 闵大洪. 从边缘媒体到主流媒体——中国网络媒体20年发展回顾[J]. 新闻与写作,2014(3):6.
[7] 付茜茜. Web3.0时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形态变迁[J]. 当代传播,2015(2):47.
[8] 大卫•贺莫斯. 媒介、科技与社会:传播理论的面向[M]. 赵伟妏,译.台北:“国立编译馆”与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19.
[9] 莱恩•考斯基马. 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M]. 单小曦,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10] 高钢. 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J]. 国际新闻界,2010(2):70.
[11]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3.
[12] 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M]. New York: Penguin Books,2004:14.
[13] 曾繁亭. 网络写手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0.
[14][16] 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47-151,159.
[15] 托马斯•福斯特. 如何阅读一本小说[M]. 梁笑,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2.
[17] Joseph P. Liu. Copyright Law’s Theory of the Consumer [J]. Boston College L. Rev.,2003(44):402.
[18] Niva E. Koren. Making Room for Consumers under the DMCA [J]. Berkeley Tech. L.J.,2007(22):1137.
[19][20] Julie E. Cohen. The Place of the User in Copyright Law [J]. Fordham L. Rev.,2005(74):347,370.
[21] Bill Werde. Defiant Downloads Rise from Underground [N]. The New York Times,2004-02-25.
[22] Natali Helberger, P. Bernt Hugenholtz. No Place Like Home for Making a Copy: Private Copying in European Copyright Law and Consumer Law [J]. Berkeley Tech. L. J.,2007(22):1061,1066.
[23] Joseph P. Liu. Copyright Law’s Theory of the Consumer [J]. Boston College L. Rev.,2003(44):400.
[24] Yochai Benkler. From Consumers to Users: Shifting the Deeper Structures of Regulation Toward Sustainable Commons and User Access [J]. Fed. Comm. L. J.,2000(52):562.
[25] Niva E. Koren. Making Room for Consumers under the DMCA [J].Berkeley Tech. L.J.,2007(22):1138.
[26] Rebecca Tushnet. Copy This Essay: How Fair Use Doctrine Harms Free Speech and How Copying Serves It [J]. Yale L.J.,2004(114):535, 566.
[27] Julie E. Cohen. The Place of the User in Copyright Law [J]. 74Fordham L. Rev.,2005(74):348-349.
[28] Joseph P. Liu. Copyright Law’s Theory of the Consumer [J]. Boston College L. Rev.,2003(44):401.
[29] Paul Goldstein. Derivative Rights and Derivative Works in Copyright [J]. J. Copyright Soc’y U.S.A.,1983(30):209,218.
[30] 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J]. Emory L.J.,1990(39):965-966.
[31] Alan L. Durham. Consumer Modification of Copyrighted Works [J]. Ind. L. J.,2006(81):853.
[32] 孙阳. 演进中的合理使用规则及其启示[J]. 知识产权,2018(10):46.
[33] Pierre N. Leval. 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 [J]. Harv. L. Rev.,1990(103):1105,1111.
[34] 熊琦. 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法释义[J]. 法学家,2019(2):124.
[35] 丹尼尔•里格尼. 贫与富:马太效应[M]. 秦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01-110.
[36] P. J. Tichenor, G. A. Donohue and C. N. Olie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0(34):159-170.
[37] 熊琦. 论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J]. 法学家,2011(1):87.
[38] 1710年英国《安妮女王法》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有关著作权法在英国的起源与发展,参见布拉德•谢尔曼,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1760-1911英国的历程[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49.
[39] Manuel Castells ed. The Network Societ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M]. London:Edward Elgar Publication,2005:20.
[40] 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35.
[41] Thomas Mclaughlin. Street Smart and Critical Theory:Listening to the Vernacular [M]. Lond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160.
[42] 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C]. 罗兰•巴特随笔选.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300-307.
[43] 易磊. 对我国当前合理使用修改的思考——以德国“合理使用”为视角[J]. 电子知识产权,2019(2):11.
[44] Pamela Samuelson. Unbundling Fair Uses [J]. Fordham L. Rev.,2009(77):2541-2542.
[45] James Boyle.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J]. SPG Law & Contemp. Probs.,2003(6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