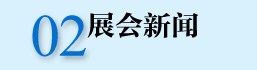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建设性"是现代新闻业存在的道德基础之一,是新闻有益于社会的基本专业信念。近年来从丹麦等国发源的"建设性新闻"运动是新闻业界和学界对新闻业如何才能更好服务社会的持续探索中的又一次引人关注的努力。从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角度出发,对"建设性新闻"运动所提出的对传统主流新闻实践中可能存在"负面偏向"问题的警惕进行考量,"建设性新闻"运动从使用者角度讨论新闻业在网络时代的新实践方式可能带来有益的启示。"建设性新闻"不是对既有新闻理念、价值和实践模式的颠覆,而是对传统新闻标准的补充。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负面偏向;新闻创新
2018年,新闻研究领域的英文期刊《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曾一次性刊登讨论“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9篇论文,介绍这组论文的导读文章在标题里问到:“为什么我们突然谈论这么多建设性?”一年之后,另一本新闻研究英文学术期刊《新闻学》(Journalism)也刊出了“建设性新闻”专辑。“建设性新闻”迅速引起国内学者的回应,2019年国内新闻学期刊密集发表了十余篇关注“建设性新闻”的学术论文,对前述两组英文期刊上的文章多有引介。2019年末召开了以“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包括“建设性新闻”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和国内学者共同研讨新闻的“建设性”,国内首个“建设性新闻研究中心”也宣告成立。这或许表明,“建设性”这样的术语在这个新闻业面临重大挑战和变革的时代尤为能够激发不同语境下的研究者探讨新闻业的问题,并站在不同的脉络中重申新闻的社会使命、畅议新闻的未来。尽管在“建设性新闻”的定义与新闻界此前已出现过的诸多“运动”或理念如“行动新闻”“好新闻”“和平新闻”“公共新闻”“方案新闻”等是何关系以及“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方式等等问题上,研究者们尚未达成“共识”,[1]但“建设性新闻”的命名正迅速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学术论文、新闻编辑部、新闻研究机构、高校新闻课程和社会化培训等机制,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当下具有较高显示度的新闻运动。
当此之时,我们有必要顺着《新闻实践》的问题再进一步追问:当全球新闻研究者都开始讨论“建设性新闻”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它的创新之处是什么?是否以及如何有可能被不同语境下的新闻行动者们采用?本文将结合学术界在“建设性新闻”主题下已发表的重要中英文文献,以及一向实行“以正面报道为主”新闻政策的中国当代新闻语境,在这些基础上初步讨论“建设性新闻”对新闻实践的理念适用性与可操作性问题。
一、“建设性”是新闻业的基本理念
阐述新闻业之社会使命与合法性的大量文献都表明,“建设性”其实是现代新闻业得以存在的重要价值支柱,是内置于新闻业的“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这在中西方新闻传统中都有明确的表达。
从中国“具有专门办报思想的第一人”[2]王韬所认为的开设报馆可解决中国“上下不通”的沉疴,到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国早期新闻思想一直把新闻业对国家社会的“功用”放在重要位置。西方新闻思想也同样看重新闻业对社会的价值。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J.Pulitzer)1904年在《北美评论》杂志上阐发对新闻业使命的滔滔宏论,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恐怕就是已成现代新闻业之隐喻的“瞭望者”说——“记者是国家这艘船驾驶台上的瞭望者”。在普利策看来,记者不仅报道可能带来危险的浅滩暗礁、大雾和风暴,也会关注好天气下海平面上出现的有趣事物、远去的风帆、并提醒船只去解救落水的人。[3]这段话在被多次转译后成了更有英雄浪漫色彩的、为国人所熟知的名言——“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浅滩,及时发出警告”。不过这也并不影响普利策要表达的原义——新闻记者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要守护社会。这,当然是“建设性”的。
“建设性”这个词也远早在眼下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开始之前,就进入到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的表述之中。如不少研究者都提到的,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W.Williams)在《报人守则》中就用了“建设性”(constructive)一词。威廉姆斯描述他所认为的最好的新闻业时同时用了“建设性”“敬畏上帝”“尊重人”等十余个限定词。[4]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更是看重“建设性”概念,[5]“建设性”应该是所有新闻报道追求的共同目标,[6]等等。
在“建设性新闻”运动中做出重要概念阐释工作的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助理教授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也认为“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源头可追溯到西方新闻理论中的“社会责任论”(Social responsibili tytheory)。她与合作者在一篇论文的开篇即引用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称新闻媒体有责任在做出新闻决策时以社会的最大利益为考量。[7]尽管报告发表后遭到了许多媒体的批评,但报告深刻阐发了新闻媒体的“自由与责任必须永远联系在一起”[8]的观念,成为支撑现代新闻业的基本价值支柱之一。
从中西方新闻理论的论述来看,“建设性”都可以说是新闻业的基本理念之一,新闻业的价值诉求就是通过专业的新闻实践活动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同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对此的表述虽有不同,但绝不会认为新闻业应该对社会发展起“破坏性”作用。不仅如此,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新闻业如何才能有益于社会。“建设性新闻”运动是在新闻学界和业界从未中断地对这一宏大命题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又一次较引人关注的努力。
二、“建设性新闻”试图改变什么?
“建设性新闻”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们试图改变或者说纠正的,是他们所认为的目前新闻业已经明显出现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的“负面偏向”(negative bias)问题。如“建设性新闻”运动的两位业界首倡者——丹麦资深记者编辑乌尔里克·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和记者出身的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Cathrine Gyldensted)都批评当下新闻业有严重的负面偏向。哈格鲁普认为,主流媒体上的新闻视角局限,太过负面,让人产生疏离感。吉尔登斯特德则试图把积极心理学作为纠正这种负面偏向的新闻实践策略。[9]受她影响,麦金泰尔做的第一篇以“建设性新闻”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就明确把积极心理学和新闻业的功能联系起来,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在新闻工作中采用积极心理学技术的新新闻形式,它致力于创造更多富有成效的、吸引人行动的新闻报道,以此真正实现新闻业的核心功能。”[10]从这些“建设性新闻”运动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不难看出,“建设性新闻”是针对他们所认为的新闻业“负面新闻过多”的痹症,采取的修复和纠正措施。
这里至少有三个前提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当代新闻业“负面新闻过多”的判断是否成立;第二,如果这一判断成立是否需要或应该被“纠正”;第三,采用“建设性新闻”倡导的诸如“积极心理学”技术是否真的有效。目前介绍“建设性新闻”运动本身状况、理念和实践的文献较多,但对这些前提深入讨论的还比较少。对当代新闻业负面新闻过多从而造成种种社会不适的批评早已出现,其中最妙的,恐怕要数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A.de Botton)在随笔集《新闻的骚动》中从一个睿智、敏感、带有精英气质的读者角度,对新闻业做的既辛辣又诙谐的批评。但新闻选择可说是新闻业运作的第一大难题,因为记者们既无法对所有发生的事件进行总体权衡后再进行选择,也无法预判新闻对千差万别的读者造成的影响。负面新闻是否“过多”,要以何为标准?谁来定标准?此外,虽然报道了“灾祸”“冲突”等具有“负面”因素的事实,但若报道中含有“救灾”“互助”和“解决方案”等“正面”因素的角度(这正是“建设性新闻”倡导的做法),是否还要被统计为“负面新闻”?这些都会成为认定上的难题。中国新闻媒体一直采用的是“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在“正面新闻”“负面新闻”“批评性报道”等实践问题上的认识,似乎比“建设性新闻”运动对“负面新闻”的理解还要更加深刻一些。如国内研究者早就提出,不能对正面报道为主方针做片面理解和僵化执行,不能因为害怕暴露问题而粉饰太平。[11]中国新闻从业者很明确地意识到新闻舆论监督应该是而且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即便是带有负面因素的新闻素材,也可以通过对负面现象的揭露,起到“反思”和“警示”的积极作用。[12]所以,新闻业“负面报道过多”这恐怕本身就是一个难以严格认定的判断,而即便是以批评和揭露社会问题为角度的“负面新闻”报道,其出发点也是对社会的警示和守护。有意思的是,本文作者发现的最早一篇冠以“建设性新闻”案例研究之名的英文论文,是1959年发表的对被认为是调查性新闻滥觞的美国新闻史上“耙粪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的分析。该研究恰恰证明,“耙粪者们身上最显著的是他们的积极观点”,他们的尖锐批判和揭露正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13]
在对新闻业“负面偏向”的批评中,“建设性新闻”运动拿出的比较有新意的观点是从新闻使用者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如麦金泰尔和其他合作者从网上招募的被试看不同的新闻报道再用问卷测量使用者的反应,结果发现在相似的议题下,那些阅读了有积极报道角度和解决方案新闻的使用者,比起接受负面框架新闻的使用者更愿意参与到推动问题解决的行动中来。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虽然负面框架下的新闻也会激发使用者的行动反应,但使用者往往期待“应该有人做点什么”,而积极框架下的新闻则更容易激发使用者自己去做点什么。[14]不过另一项用类似方式做的试验则显示,建设性新闻(在此试验中指添加了解决方案的报道)的确让使用者感到更愉快,更少沮丧,但并没有比接触非建设性角度的报道获得更多的信息,也没有让使用者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15]这两个试验应该说都还是非常初步的探索,还远不能做出确定性结论。但这些对使用者反应的研究,无论对于新闻实践还是新闻理论来说都是可贵的,因为它们给惯于采用自我阐释的方式来建立新闻理念的新闻业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实证基础。比如,当新闻业自认为揭露丑闻、腐败、警示冲突、危险、战乱是在履行对社会的守护者角色和看门狗角色时,从使用者的角度而言,是否会产生让新闻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政治冷漠、玩世不恭、虚无主义、习得性无助等,以及这其中是否有因果关系?这都是需要新闻业审慎对待的严肃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新闻”运动的确提出了好问题。但目前的探索还远远达不到重新“规范”新闻实践的程度,而且对这一角度下的经验研究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试验证明了接触建设性框架的新闻让使用者感觉更好,但让使用者感觉良好似乎并不能作为新闻业的核心诉求。尤其是上述两个试验结果还分别发现,使用者仍然认为自己更容易被负面新闻而不是正面新闻吸引,尽管后者让他们感觉更好,以及一些使用者对报道中出现的解决方案和正面例子会有些敏感,怀疑媒体是否有广告或公关的意图。“建设性新闻”运动从新闻使用者视角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新闻业使命、价值和实践方式带来了富有启发的考察。从现有的初步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新闻使用者反应方式的复杂性,但离我们真正了解新闻使用者还有相当的距离。
三、“建设性新闻”的实践难度与可能空间
研究者认为,“建设性新闻重新思考新闻职业的价值和目标,并推崇一种公共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的新闻形式,以避免在新闻文本中产生负面偏向”。[16]上文已经分析了,对“负面偏向”的判断仍有不少前提性问题有待研究,但从“建设性新闻”运动在实践上对公共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的强调,不难看出它推崇的乃是一种自我要求更高的新闻类型。如通过对“建设性新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辨别阐述,研究者认为“建设性新闻”不是“鼓吹式新闻”,“建设性新闻”提出问题的各种潜在解决方案,但仍要客观地呈现它们而非鼓吹它们。[17]“建设性新闻”也不是“服务新闻”,尽管两者在“服务受众”上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一般是文化、生活方式类的“软新闻”,而“建设性新闻”更多针对的是重要的社会议题,是用积极和建设性方式做的“硬新闻”。[18]麦金泰尔还很反对把“建设性新闻”理解为那种更重视情感和娱乐,但缺乏新闻的冲突性和影响力等主流新闻核心要素的“好新闻”“幸福新闻”。在她看来,像警察从树上解救一只猫这样的“无价值”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感觉快乐,但缺乏有意义的信息,而“建设性新闻”仍是要坚持新闻核心功能的严格报道。[19]
可以说,“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们表达了创新新闻形式、提高新闻质量、使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理想。如吉尔登斯特德建议记者们要解放思想、展开头脑风暴、改变提问题的角度、指出事情的正确方向、推动世界进步;哈格鲁普则鼓励记者在报道新闻时要建立在让读者产生:独特、亲密、被关心、获得知识和观点、觉得可信有权威、方便做决策等价值的基础上。[20]“建设性新闻”不回避社会的重大议题,但聚焦点不放在事件的戏剧性上,也不仅仅关注冲突的双方,而是需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倾听更多普通人的声音、提供事情(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这些实践策略看,“建设性新闻”主要强调记者在看待、处理和呈现新闻素材时要体现“建设性”的角度,为了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记者改变观念,而且需要记者对新闻素材挖掘得更多、对事物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这样的新闻行动策略,是否能在新闻行动者中成功扩散,取决于它能否克服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目前可看到的实践困难来自三方面:一是使用者是否更愿意使用“建设性新闻”?尽管已有一些使用者在试验的问卷调查中表达了对“建设性新闻”的“喜爱”,但这是否会转化为真实的、长期的实际新闻使用行为?目前还没有依据。二是新闻从业者可能会认为“建设性新闻”并无新意,或是无法适应当代新闻生产越来越快的时间要求,这都会增加“建设性新闻”运动在新闻媒体中的实际扩散难度。不仅在中国语境下新闻媒体一向践行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统一的方针,“建设性”的新闻报道策略早已是新闻工作的内置要求。在其他国家的语境下,记者们也表示这种理念并不新鲜,自己在以往的实践中早就这么做过。[21]真正的实践难度在于新闻生产中的时间资源如何分配。即便所有的新闻素材都可以找到“建设性”的角度,但报道时效等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也会要求先报客观事实,随后再跟进事实发展、全面呈现事实、进行深度分析、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等等。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过程式的新闻报道方法,“建设性新闻”只能是这种新闻媒体“有机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越来越快”的新闻节奏的一种自我调节,但不太可能挑战一整套建立在“时间”资源基础上的当代新闻生产常规。第三个实践困难则与“建设性新闻”的实际效果有关,也就是“建设性新闻”能否使所报道的具体社会问题有实际改善,从而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功用?毫无疑问,这仅凭记者和媒体是无法做到的。目前西方国家推行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对这一点涉及不多,似乎仍停留在努力让记者“解放思想”的理念层面上。中国媒体在这方面倒是有很多实践经验,国内学者孙五三曾相当深刻地分析过“作为治理技术的批评报道”,讨论过中国语境下“批评报道-政府行政措施-有关人员的行政或法律处理”的治理制度的建立。[22]这是批评性报道能起到“建设性”实效的一种现实路径,“建设性新闻”还有没有别的起效路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四、“建设性新闻”小议
“建设性”是现代新闻业建立和存在的道德基础之一,是新闻“有益于”社会的基本的专业信念。近年来从丹麦等国发源的“建设性新闻”运动是新闻业界和学界对新闻业如何才能更好服务社会的持续探索中的又一次引人关注的努力。“建设性新闻”运动所提出的对传统主流新闻实践中可能存在“负面偏向”问题的警惕,以及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讨论新闻业在网络时代的新实践方式,都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并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但需要明确的是,“建设性新闻”不是对既有新闻理念、价值和实践模式的颠覆,而主要是通过调整报道角度,对传统新闻模式进行纠偏。就如“建设性新闻”运动的首倡者哈格鲁普所说,“是对传统新闻标准的补充”。[23]从讨论“建设性新闻”时被研究者们频繁提及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平台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从报道议题、组织规模、在主流新闻媒体中的位置和实际影响力来看,事实上也都是“补充”而非“颠覆”。
在“建设性新闻”运动渐为全球新闻研究者所知晓之际,“建设性新闻”的语境问题也应被特别关注。“建设性新闻”运动滥觞于丹麦、荷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传播学者哈林(D.Hallin)和曼尼西(P.Mancini)曾将这些国家的媒介制度归为独特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在这种模式下“媒介被视为社会公共机构,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企业”。[24]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国民福利水平高、社会矛盾不尖锐,这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对新闻媒体如何才能更好地起到社会“建设性”作用的理解当然也会不同。此外,不同国家的媒介制度和新闻传统差异也很大,如“建设性新闻”运动所批评的主流新闻媒体的“负面偏向”问题,主要指欧美国家的主流媒体,如引介到中国语境,则不可不顾中国新闻媒体直接接受党的宣传系统领导、一贯执行“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也认为我们的传统新闻实践过多聚焦于负面、消极基调。实际上,若借“建设性新闻”运动为全球新闻研究者所关注之机,对中国媒体事实上已长期开展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进行制度探索并对“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效果进行更为清晰透彻的研究,也许能对这一运动自身做出颇有“建设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aura A & Hautakangas N.Why Do We Suddenly Talk So Much About Constructiveness?[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657-661.
[2] 黄旦 . 王韬新闻思想试论 [J]. 新闻大学,1998(3): 69-72
[3]Pulitzer J.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J].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4,178(570): 641-680
[4]Williams W.The Journalist’s creed.University of Missouri Website,http://www.journalism.missouri.edu/about/creed.html.
[5] 李彬 . 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 :责任感和建设性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3)
[6] 黄勇 . 体味新闻报道“建设性”[J]. 青年记者,2002(11)
[7]McIntyre K.& Sobel M.Reconstructing Rwanda[J].Journalism Studies,2018,19(14): 2126-2147
[8] 哈钦斯委员会 .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C]. 展江,等,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6
[9]Kovacevic P & Perisin T.The potential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deas in a Croatian context[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47-763
[10]McIntyre K.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D].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2015:7
[11] 唐绪军 . 西方媒体“好新闻”的实践、理论及借鉴 [J]. 对外传播,2015(11)
[12] 刘振 . 浅议负面新闻信息的建设性报道 [J]. 今传媒,2010(9)
[13]Chalmers D M.The Muckrakers and the growth of corporate power: A Stud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59,18(3): 295-311
[14]Baden D,McIntyre K & Homberg F.The Impact of Constructive News on Affective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s[J].Journalism Studies,2019,20(13): 1940-1959
[15]Meier K.How does the audience respond to constructive journalism?[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64-780
[16]Hermans L & Drok N.Plac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context.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679-694
[17]Aitamurto T & Varma A.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journalism[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695-713
[18]From U & Kristensen N.Rethink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y means of service journalism[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14-729
[19] 晏青,凯伦•麦金泰尔 . 建设性新闻 :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 [J]. 编辑之友,2017(8)
[20]From U & Kristensen N.Rethink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y means of service journalism[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14-729
[21]Kovacevic P & Perisin T.The potential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deas in a Croatian context[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47-763
[22] 孙五三 . 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 - 社会运作机制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1)
[23]From U & Kristensen N.Rethink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y means of servic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 714-729
[24] 丹尼尔•C•哈林,保罗•曼奇尼 . 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M]. 陈娟,展江,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