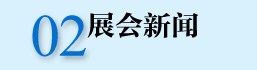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摘 要】基于现有对建设性新闻的学术讨论,描述这一概念的缘起与发展、渊源与分类、效果与评价、创新与坚守等多个面向,试图呈现这一新闻研究领域新兴议题的建构过程。经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试图通过建设性的报道技巧和积极情感的引入重塑新闻业的权威与合法性,因而成为当前新闻业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变迁,但这一创新实际是一种重新引介的传统。当下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不是为了解决它的未来存续问题,而是试图借助这一透镜来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业。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负面偏向;新闻创新;公共服务
传统新闻业仍处在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的升级、渠道的扩充、内容的丰富等积极面向,也会带来营收的下滑、信息的过载、受众的脱节、信任的流失等问题。新闻业试图通过各种创新的举措来缓解乃至对抗上述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正在兴起的建设性新闻运动也是一种新闻创新。它试图纠正以往新闻业所具有的负面偏向(negativity bias),通过建设性的报道技巧和积极情感的引入,提供更为优质的新闻,加强与受众之间的连接,重塑新闻业的权威与合法性。近年来,建设性新闻已经在欧洲、北美、亚洲、非洲等不同政经环境下的国家得到了实践,甚至溢出新闻业界,成为新闻研究者着力讨论的新兴议题。
一、建设性新闻的缘起与发展
建设性新闻是一场缘起于新闻业界的改革运动。2008年,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新闻主管乌尔里克·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在丹麦报纸上首次提出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与倡议。他主张“未来的记者应该采用建设性的新闻标准,补充传统新闻价值观。解决方案与灵感以及其他有建设性效应的故事可以平衡关于死亡、毁灭和社会苦难的故事。”[1]随后,哈格鲁普继续通过著书立说、成立研究所的方式积极推介建设性新闻的理念。2014年,英文作品《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News)的出版则让建设性新闻理念进一步进入英语世界的从业者与研究者的视野中。
在哈格鲁普于2008年首次发出建设性新闻的倡议后,建设性新闻在实践中逐渐体现出基于“专业网络”运作的特点,[2]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闻机构按照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进行新闻生产。二是大学、新闻从业者成立的非盈利机构积极推进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与教育。2016年,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新闻系发展了建设性新闻的六大要素:解决特定问题,在报道问题的同时增添解决方案;以未来为导向,在传统的5W的基础上增加“现在怎么办”(what now);包容性与多样性,包含更多的声音与视角;公民赋权,赋予受害者与专家权力,询问可能的资源、合作、共同点以及解决办法;解释新闻语境,从报道事件到报道语境;共同创造,赋权于公众,与市民共同参与新闻内容的创作。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Cathrine Gyldensted)等人总结了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导向,分别是公众导向(public-oreiented)、方案导向(solution-oriented)、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和行动导向(action-oriented)。[3]目前,一个包含出版、会议、新闻、课程、学人项目、研究计划不同形式在内的建设性新闻运动正在兴起。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现实:其一,建设性新闻的流行仍局限在特定区域,主要是西北欧的少数国家;其二是建设性新闻还主要停留在话语层面,尚未形成一系列连贯和可识别的实践。[4]
事实上,关于建设性新闻本身就存在两种说法。哈格鲁普常用的术语是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news),偏向通过新闻故事的选择和报道生产建设性新闻,关注建设性如何成为新闻的标准与框架。另一位建设性新闻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吉尔登斯特德常用的术语是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着眼于建设性新闻的影响,这与她对积极心理学的倡议是一致的。[5]简单来说,前者关注的是建设性在新闻文本中的体现,而后者更看重建设性的理念和技巧在新闻实践中的运用。比较而言,后者正逐步获得更大程度的接受和认可,成为当前研究此类新闻现象的主导性术语。
除了来自新闻工作者在实践层面的呼吁和探索,将其纳入新闻研究的学术视野,对其进行学术话语的建构也是塑造这一“创新”的合法性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哈格鲁普对建设性新闻的阐释是在新闻的社会责任框架下进行的,依然是一种行业话语的论述。而在建设性新闻由新闻实践进入学术话语的过程中,吉尔登斯特德和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吉尔登斯特德此前也是一位丹麦记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以后,她发现心理学中的积极心理学可以指导建设性新闻的实践。积极心理学是对传统心理学关注病理与精神疾病的转向,最突出的研究领域是复原能力、品质美德、幸福感、创伤后成长、积极情绪、爱和展望等。[6]面对主流新闻报道遵行的“世界的疾病模式”(the disease model of the world),积极心理学倡导的是“世界的幸福模式”(the well-being model of the world),[7]这与建设性新闻的目标不谋而合。积极心理学的引入为建设性新闻赋予了更具限制性的界定,也成为与其他相似新闻实践进行区分的重要标准,使得这一实践具有了学理基础。[8]通过对哈格鲁普与吉尔登斯特德建设性理念的分析,布罗(Bro)认为哈格鲁普更倾向于被动的新闻角色,制作的新闻关注私人,有时代表政治家与企业领导人。而吉尔登斯特德更偏向激进,也同时关注公民与决策者。[9]继吉尔登斯特德之后,麦金泰尔将积极心理学与建设性新闻进行了更为深度的勾连,她于201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积极情绪与解决方案新闻的效果。此后几年内,她又相继发表了多篇与建设性新闻相关的论文。根据徐敬宏等人的统计,在建设性新闻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中,麦金泰尔和吉尔登斯特德分别以6篇和3篇的发表数量居于前两位,[10]显示了两人在建设性新闻研究领域的关键地位。
二、建设性新闻的渊源与分类
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新闻实践,建设性新闻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新闻学界的关注。尤其是2018年以来迎来了建设性新闻研究的一个高潮,SSCI期刊《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新闻学》(Journalism)相继刊发了讨论建设性新闻的专题。研究者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界定、应用分析、受众效果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仍处于学术研究的早期阶段,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为这一新兴实践确立合法性的色彩。
首先,研究者更为着力开展的一项工作是发掘其历史根基,以论证其学术价值。布罗将建设性新闻的先驱追溯至百年前威廉(Williams)在《记者信条》中的倡导和普利策(Pulitzer)的行动新闻实践。威廉最早指出了优质新闻业的建设性特征,普利策阐明新闻业要提供“公共财富”与“公共善”以确保新闻业的建设性。[11]克鲁格(Kruger)将建设性新闻追溯至1948年,纽约“好消息公告”的新闻服务机构专注于“成功的项目和积极的替代性方案”。[12]埃塔穆托(Aitamurto)和瓦尔玛(Varma)将扒粪运动、公共新闻、和平新闻、激进新闻都视作建设性新闻的起源与先例。[13]从这些不同说法可以看出,研究者普遍认为新闻业中原本就内嵌着建设性的成分,在过往的历史中曾有不同程度的展现,而建设性新闻只是新闻业的建设性形式的一种最新呈现。建设性新闻的本质同样是公共服务,与它所批判的以负面偏向为特征的客观新闻业并无区别,只是新闻业的发展偏向了公共服务应该基于建设性的路径。[14]因此,也有人认为,建设性的讨论只是一种新闻业旧形式的复兴,并非新理念发明。[15]
其次,正是由于建设性新闻具有漫长的历史脉络,研究者发掘出多个具有“建设性”的新闻形式,都与建设性新闻有很强的关联。因此,研究者不得不通过对这些相互交叉的概念进行比较来厘清建设性新闻。麦金泰尔与吉尔登斯特德将建设性新闻定义为“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它将积极心理学的技术应用到新闻过程和生产中,努力创造富有成效和参与性的报道,同时也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她们以积极心理学策略的应用为标准,认为建设性新闻存在解决方案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前瞻性新闻(prospective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与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narrative)四种分支。这些分支概念相互之间并不冲突,甚至不乏交集之处,构成了一个“伞状”的概念体系。[16]其中,解决方案新闻的出现远远早于建设性新闻,早在20年前,解决方案新闻就已经在美国兴起,其报道框架集中在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上,试图为变革提供蓝图,改变公共话语的基调。解决方案新闻一定具有建设性,但并非所有的建设性新闻都要给予解决方案。[17]前瞻性新闻关注面向未来的新闻业,新闻工作者可以将想象未来的能力应用到新闻工作中。而和平新闻的理念指的是在报道中为整个社会创造机会,考虑和重视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恢复性叙事指的是以一种更具恢复性的叙事来报道社区冲突。[18]
无论是发掘建设性新闻的历史根基,还是在相近的新闻实践之间进行区分,研究者着力开展的都是对建设性新闻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工作。目前采取的策略仍是一种很宽泛的界定方式,宽泛定义的好处是允许不同研究者思考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及其对社会的益处,问题则在于对研究者来说这一概念不是很具有操作性。[19]因此,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界定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研究者一方面继续对建设性新闻这一统摄性概念进行阐释,比如将其放在服务新闻(service journalism)[20]和社会责任新闻(socially responsible journalism)的脉络下理解,[21]或是把影响力(impact)当做区分建设性新闻与传统新闻形式的明确标准[22];另一方面则对其中的若干分支概念做进一步的概念化,比如对方案新闻进行更清晰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尝试。[23]
三、建设性新闻的效果与评价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理念和实践得以扩散的关键因素在于它究竟能否产生所声称的效果。因此,在对建设性新闻进行实证分析时,研究者目前主要集中进行了两类研究:第一类主要讨论的是新闻业的建设性形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第二类是关注不同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对建设性报道方式的评价。[24]这恰好对应着建设性新闻实践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体:建设性新闻的阅读者和生产者,他们对建设性新闻的接纳最终将决定这一创新能否延续下去。
自麦金泰尔的博士论文开始,建设性新闻的经验研究就显示出极强的效果研究取向。她通过对164名学生的在线调查研究发现,对社会问题提及有效的解决方案会让读者感觉更好,但对读者的行为意向或实际行为并不会产生影响。[25]迈耶(Meier)结合访谈与实验法研究建设性新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影响。在微观层面,读者可以认识到建设性新闻的希望、鼓励、安慰和解决方案等特质,虽然读者情绪更佳,但对新闻并没有更好的了解与更大的兴趣。中观层面,建设性报道更容易被社交网络分享,但人们并未对发布建设性新闻的新闻机构持有更高的忠诚度。在宏观层面,建设性报道并不能带来行动意愿,但对建设性报道的分享意愿长期可以提高人们对解决方法的认识。[26]克里曼斯(Kleemans)等人探究了建设性新闻与非建设性新闻在儿童对负面新闻的回忆上的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相比非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的负面新闻内容在记忆中不那么明显,受访儿童更多回忆起建设性的部分,建设性新闻消解了儿童对负面新闻的关注。[27]赫尔曼斯(Hermans)和吉尔登斯特德在线调查了超过3000名荷兰人对于建设性新闻的认知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于认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闻中的建设性因素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那些传统媒体不太重视的人群:年轻人、中低教育程度以及对新闻不太感兴趣的群体。[28]
对建设性新闻的倡导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新闻中的负面消极内容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于受众阅读建设性新闻的效果进行研究,既可以对其效果有一般性的了解,也可以对建设性新闻理念本身的合法性进行检验。从上述对建设性新闻效果研究的结果来看,相较非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可以降低人们对新闻以及新闻所报道事件的消极态度,但这并不会转化成为行动意愿以及行动。人们已经关注到了新闻中的建设性因素,同时警惕建设性新闻中可能包含的广告与公关元素。
虽然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发源于欧洲,目前明确以建设性为理念指引的实践项目也多集中在欧美,但对于建设性新闻实践的研究对象却主要集中在处于转型期的非西方国家新闻业,尤其关注的是这些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对于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认知情况。科瓦切维奇(Kovacevic)和佩里辛(Perisin)研究了克罗地亚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识以及新闻实践的建设性成分。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的概念总体上被新闻从业者接受,但克罗地亚语境中的建设性新闻也可能意味着不加批判。因此,对建设性理念在克罗地亚新闻业的传播与教育必须基于对理念独特性的清晰且深入的解释。[29]麦金泰尔和索贝尔(Sobel)调查了种族大屠杀后的卢旺达记者的角色认知与对建设性新闻技巧的使用。研究发现,卢旺达的记者与西方国家记者一样,重视新闻的告知与教育等传统角色。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处于冲突恢复时期的卢旺达,记者还将促进团结与和解作为自身的义务,比西方记者更重视社会利益。[30]罗特梅耶(Rotmeijer)对加勒比海地区圣马丁岛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研究在后殖民主义国家践行建设性新闻的意义与可行性。通过对记者、编辑以及新闻博客作者的深入访谈发现,基于促进经济发展、参与、归属以及社会稳定的理想,圣马丁岛已经普遍开展了建设性新闻实践。然而,由于后殖民的政治背景、新闻业对商业的依赖、沉默的威权文化环境等原因,建设性新闻很有可能仅仅是对现状的反映,甚至可能落入当权者的手中。[31]阿拉姆(Allam)通过对21名埃及与突尼斯记者的访谈,探究了建设性新闻在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作用。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在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发挥着重新赢得受众信任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服务公众利益和振兴主流媒体经济等多重意义。然而其成功实施也受到当地政治权力结构、私有制以及建设性概念本身可能存在的负面意涵的影响。[32]
针对这些国家的新闻业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记者对于建设性新闻的认知、建设性新闻实施的可能性以及建设性方法的使用与作用。既有研究已经发现,转型期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同时拥有新闻专业的传统精神,但具有更积极的角色认知,他们觉得更有责任帮助冲突后的社会转型,努力促进社会变革、教育公众。[33]由于这些国家的新闻文化本身就蕴含有较强的新闻业干预、介入、参与、影响社会现实的传统,因此与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有高度契合之处。尽管这些国家的新闻业并未公开追随建设性新闻理念,但由于其特殊的新闻业环境,其实践中已经含有建设性新闻的成分。
四、建设性新闻的创新与坚守
建设性新闻是数字媒体时代的产物,成为当前新闻业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变迁。但这一创新并不是全新的理念,而是一种重新引介的传统。一方面,在新闻业的发展历史上,并不缺乏相似的理念与实践,行动新闻、公共新闻、公民新闻、解决方案新闻等蕴含建设性的新闻实践早已有之;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的建设性新闻运动赋予了建设性相对清晰的概念界定,包括积极心理学的技术应用,以及公众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与行动导向的建设性思维。
新闻中的建设性在新闻业的不同传统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这种建设性在实践中日益被忽略。尤其是在70年代水门事件与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事件之后,新闻业就确立了批判性报道的传统。[34]新闻记者在提醒公众注意威胁、揭露政府腐败以及迎合受众兴趣的过程中陷入了对消极负面新闻的生产。而多项研究与调查表明,负面新闻会对受众产生负面影响。[35]近年来,新闻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公共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出现,全球化带来地方身份与社区的重新评价,新的虚拟社区的形成以及社会距离的缩小。这些都为新闻业带来了全新的经济环境、技术环境与公共领域。在新闻业面临的种种困境中,尤为严重的是与公众失去联系而导致的信任危机,重塑公众信任因此成为了新闻业面临的主要挑战。[36]在实践中,建设性可以被看作是专业新闻业自身的权威流失的一种反应。[37]
建设性新闻试图通过对客观新闻中的“负面偏向”的挑战而对主流的新闻范式形成有益的补充。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规范性标准基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38]虽然它被建构为西方主流新闻业的核心,但新闻业对于另类规范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此前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公共新闻运动,它应对的就是新闻业与公众关联和信任的失落问题,主张记者应该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发表内容,并帮助社会采取行动。[39]建设性新闻与公共新闻的理念存在极强的相似性,二者都强调新闻业要帮助社区解决问题而非仅仅告知,使用面向解决方案的框架与信息,将受众视为积极公民。建设性新闻之所以从丹麦率先起步,就与该国具有深厚的公共新闻传统有关。但与此同时,它们仍然要满足客观性,实现新闻的核心功能。建设性新闻强调以建设性方案代替对冲突性的报道,尽量在保证客观性的基础上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只是在严格遵守传统新闻实践和规范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建设性角色的维度。[40]可以说,建设性新闻的内核是传统的,只是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在新闻业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新闻创新的改革运动,但以往的很多运动都消失了,只是在研究者中留下印记,而在实践者中不流行。阿哈瓦(Ahva)等人建议将建设性新闻运动置于新闻业自我修正的视角与脉络之下。[41]既然是一种自我修正,那么它解决的只是某个特殊时刻的问题,持续或消逝都是可能的命运。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新闻业的规则与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并且存在极大的一致性与可变性。新闻业的构成性规则并未限制记者以任何特定的方式进行报道,只要可以让他人接受其实践的合法性,几乎任何类型的新闻都有可能是适当的。[42]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不是为了解决它的未来存续问题,而是试图借助这一透镜来理解变革中的新闻业。
参考文献:
[1]https://politiken.dk/debat/kroniken/art5471819/Konstruktive-nyheder
[2][41]Ahva,L.,& Hautakangas,M.(2018).Why Do We Suddenly Talk So Much About Constructiveness?.Journalism Practice,12(6),657-661
[3][28][34]Hermans,L.,& Gyldensted,C.(2019).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Journalism,20(4) 535-551
[4][22]Wagemans,A.,Witschge,T.,& Harbers,F.(2019).Impact as driving force of journalistic and social change.Journalism,20(4),552-567
[5][9][11][14][39]Bro,P.(2019).Constructive journalism:Proponents,precedents,and principles .Journalism,20(4),504-519
[6][8]McIntyre,K.,& Gyldensted,C.(2018).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662-678
[7]Gyldensted,C.(2011).Innovating News Journalism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y
[10]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等 . 建设性新闻 :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 [J]. 国际新闻界,2019(8)
[12]Uwe,K.(2017).Constructive News: A New Journalistic Genre Emerging in a Time of Multiple Crises.The Future Information Society: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blems.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403-422
[13][15][40]Aitamurto,T.,& Varma,A.(2018).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695-713
[16][18][35]Mclntyre,K.,& Gyldensted,C.(2017).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4(2),20-34
[17][30]McIntyre,K.,& Sobel,M.(2018) Reconstructing Rwanda.Journalism Studies,19(14),2126-2147
[19]Wiard,V.,& Simonson,M.(2019).“The city is ours,so let’s talk about it”: Constructing a citizen media initiative in Brussels.Journalism,20(4),617-631
[20][37]From,U.,& Kristensen,N.N.(2018).Rethink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y Means of Servic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714-729
[21]Hautakangas,M,,& Ahva,L.(2018).Introducing a New Form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730-746
[23]McIntyre,K.,& Lough,K.(2019).Toward a clearer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solutions journalism.Journalism,DOI: 10.1177/1464884918820756[24]Nölleke ,D.(2019).Constructive Journalism.In Vos T.,& Hanusch,F.(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Journalism Studies(pp.341-344).New York: Wiley
[25]Mclntyre,K.(2015).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6]Meier,L.(2018).How Does the Audience Respond to Constructiv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764-780
[27]Kleemans,M.,Dohmen,R.,Schlindwein,L.F.,Tamboer,S.L.,de Leeuw,R.NH.,& Buijzen,M.(2019).Children's cognitive responses to constructive television news.Journalism ,20(4),568-582
[29]Kovacevic,P.,& Perisin,T.(2018).The Potential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deas in a Croatian Context.Journalism Practice,12(6),747-763
[31]Rotmeijer,S.(2019).“Words that work?” Practice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a local Caribbean context.Journalism,20(4),600-616
[32]Allam,R.(2019).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Arab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 Perceptions,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Journalism Practice,13(10),1273-1293
[33]Anderson,K,Kenneth,H.A.,& Godole,J.(2017).New Roles for Media in the Western Balkans.Journalism Studies,18 (5),614–628
[36]Hermans,L.,& Drok,N.(2018).Plac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Context.Journalism Practice,12(6),679-694
[38]Schudson,M.(2001).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Journalism,2(2),149-170
[42]Ryfe,D.(2006)The Nature of News Rules.Political Communication,23(2),20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