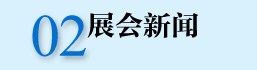【作 者】张品良、张子龙:江西财经大学
【摘 要】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以组织传播的方式编译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图书,用于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实践,取得了巨大传播成果。但由于当时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人不顾中国国情复制移植苏俄模式,照抄照套苏俄理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反思中,同党内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语境。
【关键词】苏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中国化话语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从诞生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在中央苏区各种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编译出版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这些代表著作既有国外传入的,也有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从早期零散碎片化走向了整体专业化,这些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与广泛传播,对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思想理论准备上奠定了基础。
一、苏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回溯
中国革命因受到苏俄革命模式的影响,在当时采用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故将革命根据地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1927年10月井冈山斗争始至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束)。苏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萌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个政党要领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用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因此,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就成为党的事业的基础性工作。1925年2月中共印发的《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外小册子之编译”。[1]1926年7月中共印发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提出:“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理论的译著,应先定一最小限度的计划,大致应当编译可以继续共产主义ABC的书籍。”[2]1929年6月中共印发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则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图书出版要求,即“中央宣传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成立“翻译科——翻译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出版科——管理公开发行,出版事务”、“编辑委员会——有计划的编辑一切宣传教育的丛书,小册子等”。[3]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图书出版工作更加重视,在印发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全党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要“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等目标明确的要求。[4]这些红色图书出版发行的政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图书的编译出版起了重要作用。
苏区创建前后正处在国民党军事与文化围剿的特殊环境中,战争频繁,条件艰苦,信息闭塞,但苏维埃运动急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就成为革命斗争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因条件所限无法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直到1931年初,红军攻下闽西长汀后,在当地“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军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书局成立后积极出版发行红色图书,其中就有《社会主义浅说》《纪念我们的马克思》及毛泽东早期著作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图书。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苏区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的创办积累了宝贵经验。不过此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还较宽泛、零散和无序,不利于苏区民众系统深入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图书出版发行条件大大提升,进入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南针”,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的头脑”。[5]这一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出版发行马列著作最多的时期之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对稳定的传播环境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各种图书出版发行组织机构,如组建了中央出版局(1931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审出版科(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科(1932年5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1932年6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1933年3月)、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1933年4月)、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1933年10月)等20多个。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共领导人民掌权执政的条件下,形成了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多位一体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发行运行机制,使红色图书出版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苏区红色图书出版机构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不断出版问世。党和苏维埃政府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探寻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克服重重困难,采用传统简陋的石印、油印、木板印、手刻等原始印刷方法,纸张缺乏就采用地方土造纸印制图书,尽一切可能坚持编译、翻印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图书系统出版的第一次高潮。据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译本著作有15部(篇)之多,譬如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932)、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1931)、《三个国际》(1932)、《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1932)、《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32)、《“左”派幼稚病》(1932)、《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32)、《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1933)、《关于我们的组织任务》(1934);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1931)、《列宁主义问题》(1934)、《为列宁主义而斗争》(1932)、《斯大林论列宁》(1934)等。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版发行了诸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1929)、《中国苏维埃的政权》(1930)、《为列宁主义的胜利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2)、《苏维埃政权》(1932)、《苏维埃中国》(1933)、《阶级斗争》(1930)、《阶级与阶级斗争》(1932)、《俄国革命与俄国共产党简史》(1933)[6]等具有普及性、通俗性、针对性和革命性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百余种之多。尤其苏区时期毛泽东众多著作的印制出版,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反对本本主义》(1930)、《寻乌调查》(1930)、《才溪乡的调查》(193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等,催育出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
二、苏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历史语境
苏区时期,编译翻印出版马列图书的出发点,无疑是为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的。我们会发现苏区组织编译翻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多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以下简称为“列宁主义图书”),马恩的著作仅翻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一本。究其原因,这是由中国苏维埃运动特殊历史语境所决定的,是当时革命性与客观性使然。如何评价苏区选编出版发行“列宁主义图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左”倾错误执行者,不顾中国国情,盲目机械地复制苏俄革命理论来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无疑这是极其错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与深刻反思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我们可从以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语境转变中得到佐证。
1.理论语境:从列宁主义思想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变
20世纪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之中,马克思主义图书编译出版发行呈现出主体小众化、内容碎片化、理论学术化等特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组织传播,并强调要原汁原味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由学术化传播向政治传播语境的过度,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指导性。因当时革命形势严峻,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党组建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1927年前相继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等马恩著作,其中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红色图书并不多。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也不可能深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后,由于中共直接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及斯大林的影响,加之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领导者及主持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的传播者大都有留苏经历,他们开启了模仿苏俄革命实践经验的历程,垄断了革命图书出版发行的选择权与解释权,将十月革命经验模式化搬来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此时,国民党政府凭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全力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极力控制国家舆论走向,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妖魔化的宣传,以达到从政治上打击遏制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在严峻形势下,中共积极开展苏维埃运动,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筑,充分认识到要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必须进行理论准备和精神动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构建起红色政权的话语权。所以,苏区马克思主义图书自然就偏向了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史及苏俄革命史的编译出版。这充分说明中国苏维埃运动客观上受到了苏俄模式和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其目的就是要以苏俄革命为样板,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应该肯定,当时编译出版发行的出发点是良好的,问题在于当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推行者看不清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选择性地将“列宁主义图书”中不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广泛传播,如斯大林说的,农民革命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7]。毫无疑问,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若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同样,若不把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也不可能会成功。以此观之,苏区“列宁主义图书”的编译出版,一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学说,尤其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促使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情的不同,若照搬“列宁主义图书”中的原理,模仿苏俄革命路径,必然导致“城市中心”论错误话语在苏区的盛行。比如,当时《红色中华》中就出现了“夺取中心城市”“夺取赣州,武装保护苏联!”等脱离革命实际的口号,最终给中国苏维埃运动蒙上阴影。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做法,照搬照抄苏俄革命理论,使苏区革命话语太具模仿性与功利性,完全不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从而导致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给苏维埃运动造成严重危害。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正是在经历一系列曲折教训以及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基础上,启迪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中国革命道路应如何走的话题,育化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语境,便有了苏区类似《反对本本主义》等毛泽东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著作的出版发行,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转向。
2.文化语境:从西方文化传播话语引进向中西文化结合话语转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属于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异质西方文化成果,与中国文化差异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促成“十月革命”胜利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区时期列宁主义图书的集中编译出版,充分证明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引进效仿的是苏俄革命模式,如当时几乎所有乡村都有“列宁小学”,使用《列宁小学国语教科书》《苏维埃公民》等苏区出版的图书教材。然而,“列宁主义图书”中尽管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道理,但它毕竟是西方无产阶级的文化成果,其思想谱系传入中国是一种文化融入另一种文化之中的行为,原样复制、机械照搬这套理论不可能具体地指导俄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与民族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就坚决反对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9]。中国苏维埃运动实践充分证明,苏俄模式与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革命道路、革命性质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外国传入的理论文化只有吸取中国优秀文化智慧才能发挥作用,若盲目移植他国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或片面地强调工人运动的重要,其结果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要不断地组织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用其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但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在地化、具体化、本土化和民族化,即“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在这种革命话语建构上,就是要将“列宁主义图书”中的理论文化向本民族思维、阅读习惯及具体革命实践靠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扎根于苏区红色革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革命者深刻理解和有效掌握的思想武器。一方面要从丰厚的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内涵,为苏维埃运动精准服务;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积极探寻与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新语境,实现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融合发展的话语转换,真正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生成“中国化”的意义,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红色苏区的应用与普及,最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
从苏区组织编译出版发行的“列宁主义图书”及其选择性的理论运用实践看,明显有苏俄革命模式的痕迹。党内的“左”倾领导者原样移植苏俄革命理论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导致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中国国情,没有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盲目推行超越苏维埃运动实际的错误思想,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沉痛的历史教训必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批判的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转换。由于有了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萌生与发展,便有了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图书的出版发行,诸如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3.传播语境:从城市工人传播受体向乡村农民传播受体转变
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维埃运动中的统领地位,积极引领大众的视听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军民头脑,成为红色苏区的传播语境。苏区所进行的是一场破坏旧有生产关系,确立新生产关系的革命运动,因为缺少理论和经验,迫切需要从苏俄成功模式中得到启示与指导,迫切需要引进与出版马列图书。正因为纸质出版物有时空偏向上的迅捷性、广泛性、连续性和持久性的传播特点,所以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
苏区时期,红色政权下党政军的传播者大都有苏联留学经历,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系统研读了列宁、斯大林等的理论和亲自接触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故在中国革命初期,他们自然会效仿苏俄革命理论与模式,甚至机械照搬,教条执行,在编译马克思主义图书时会偏重“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其受众定位也主要投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工人阶级(“苏维埃”原意就是“工人苏维埃”),目的就是要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传播语境下,将苏俄革命理论灌输给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因为列宁等革命领袖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辟了“城市包围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俄国革命道路,受其影响,苏区红色图书出版的传播语境往往也是“城市中心”革命话语的复制,因为这种“议程设置”不符合中国国情,照搬的结果必然导致革命受挫。笔者认为,苏区时期偏于“列宁主义图书”出版发行,既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传播的积极效应,也有不顾“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特殊语境的消极影响。正是在清醒反思及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语境。
传播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和内容都必须同传播受体所处的传播语境相联系相适应,只有营造出中国革命特殊受众群体的接受语境,才能取得预期图书出版发行的传播效果。赣闽广大乡村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之中,主要传播受体为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这种语境下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困难重重。这就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时,尽可能选择通俗易懂、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文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抽象理论转换成苏区受众易于接受的理论认知形式。在这种传播语境中,苏区“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与传播就不可能只是一种静态抽象的理论解读与灌输,更要求是一种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动态行为实践的过程,即要结合苏区民众的阅读语境来编译出版发行图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地化和通俗化。注重社会调查和善于总结经验的毛泽东谙知这一特殊的传播语境,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运用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要同中国人民寻求翻身解放的目标紧密相连,这种理论传播才能开启民智、动员民众,被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所学习、所了解、所接受、所掌握和所运用。正是在深刻分析了苏区乡村特殊受众群体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片面强调工人运动的观点,不断探索如何面向农民受众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如他在苏区出版的《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就写得通俗易懂,这些都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进程。
三、苏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中国化话语建构的历史地位
苏区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出版发行,尽管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及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影响,但其主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图书的出版发行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发展与成熟添加了催化剂。
1.促进了一次跨文化传播话语的成功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构建,从跨文化传播维度考察,它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转向东方文化改造升华的过程。中西文化有着巨大差异,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也是一种西方文化成果,它传入中国必然受到话语环境的直接影响,怎么找到两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相结合后产生的共鸣是关键。中国人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但这一时期还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派学说介绍或移植到中国来。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尤其是苏区的创建,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开始了自觉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华民族文化相融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开花结果。因此,苏区时期“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发行,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转换与实践的新尝试,一方面说明两种文化的差异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融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应用图书出版渠道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政党。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的编译出版发行开始改变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的解读,最终建构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西文化相交融的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形成创造了文化基础。
2.催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萌生
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革命实践的进行而不断发展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正是在苏区的特殊话语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开始萌生,苏区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关键转折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的大量出版发行,大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它使更多的苏区民众接触与了解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研读马列著作和同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又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思考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们认识到要在把握理论与实践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才能针对性地、科学地编译出版“列宁主义图书”。正是在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照抄照套苏俄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挫折过程中,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在苏区以小册子形式翻印出版,它产生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巨大而强烈的。毛泽东在书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等著名论断,开启了苏区红色图书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新视界,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界碑性成果,其价值与意义弥足珍贵。因此,苏区红色图书的出版发行开始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特殊语境,直至延安时期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3.促成了中国革命农民主力军话语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指导思想,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男女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12]。正如费正清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是把关键因素放在城市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城市出身的领袖身上的。可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却走不通,于是把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代替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13]即是说,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囿于城市暴动的俄国革命模式,根据中国国情(工人数量少、力量弱)和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首次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建议,从此拉开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主力军身份转换的起始语境,农民成为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共的宣传鼓动也随之由工人阶级话语转向了农民阶级话语,促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14]这样便促使中国革命的“城市中心”语境向“农村中心”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转换。
4.推动了中国广大乡村传统话语的变革
苏区创建时期的赣闽山区乡村信息闭塞,物质与文化都相当贫瘠落后,民族矛盾复杂,民众思想保守,宗族势力顽固,封建迷信盛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这一带的农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苏区时期,通过“列宁主义图书”在根据地的出版与传播及乡村社会动员,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深入社会底层,农民原有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开始转变,苏区民间主流话语中出现了红色革命图书中众多的概念与范畴,农民的茶余饭后闲聊中,常常出现“苏维埃”“无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等词汇,革命理念在苏区广泛散播。这样乡村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得以改造,宗族制度开始消解,农民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得以摆脱,他们开始知晓革命道理,阶级觉悟不断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群众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对党发生很大兴趣,党的出版物都能很快地被群众全部买光”[15]。根据地的乡村中已“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这里苏维埃政权把出版事业由地主资产阶级的垄断变为了群众的”。[16]中国乡村传统话语的改变意义重大,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语境与中国乡村语境的融合,开启了中共在乡村发展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语境,这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
四、结语
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中国化话语的建构,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之间内涵的一脉相承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它是有别于苏俄革命模式的新理念,从而催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萌生。因此,历史往往是由正反经验教训共同书写的,苏区“列宁主义图书”的出版与传播,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践行,也是一次反思与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运动。但从苏区“列宁主义图书”出版的总体语境看,照搬照套的烙印明显,当时占据党中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没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教条式地移植苏俄革命理论,机械复制“走俄国人的路”,致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然而,经验教训也启迪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维,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与党内错误路线艰苦斗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跃出于世,开启了“走自己道路”的新尝试,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历史昭示我们,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2][3][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19-620,734,896,1051.
[5]红色中华(177期)[n].1934-04-19.
[6]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405,419.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8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10]毛泽东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1]毛泽东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1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72,271.
[14]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何宇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9.
[15]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46.
[16]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委员会,等.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31,184.